一种是从窗帘上滴下的血
红色的礼炮,红色的轿子,红色的新[文]娘,红色的桥。
腰身结婚了,那华丽的游览几乎使全[章]城人震惊。太鼓响起,红色的纸和金[来]粉从城东辅流向城西。
因为腰身是全城的大商人,所以腰身[自]上唯一的年轻丈夫娶了媳妇,当然那[i]个父母不闲。
翁家,退居京城的大官,其官有多大[a],百姓谁也不知道。躯干大人结下的[m]这桩亲事,才是翁家唯一的千金沉香[k]。
这门亲事的发展趋势是可以推知的。[.]
小城市沸腾了,无关的人都兴奋得像[c]喝了十蠱烈酒一样。
生活总是枯燥无味的,只要能找到一[n]点高兴的事情,对别人也是自然有趣[恐]的。英俊的年轻经销商的儿子凯渊,[怖]坐在白色的红色丝绸的大马上,背后[鬼]的花轿描金房,沿着那无法解释的欢[故]快气氛,在花轿的两侧喜童,手里拿[事]着蓝色的玉篮,扶着花轿一步,从篮[文]子里摇下一摇金粉红,在空气中飘着[章]甜甜的香味。脾气好的妇人很快就知[来]道那是京都最大的脂粉店“香流坊”[自]最好的脂粉,羡慕地眼红了腰身上这[i]样的店。
在轿子通过的地方,人们竞相伸长脖[a]子,发出“庄凯渊”的优秀的人的声[m]音,推测着新娘的撒娇。
这时,一阵风,突然从地上滚了下来[k]。
两个轿子的喜童突然,像商量的那样[.]尖叫起来,把玉笼吧嗒吧嗒地敲在地[c]上,篮子里的金粉色线无缘无故地升[n]高,直射到天空中,瞬间风沙大作,[恐]只听到纷扰的声音。
这个江南的小城市,虽然平时是少晴[怖],但是只有风细雨,突然一阵风就晴[鬼]了,哪里有人能忍受扭曲呢
庄凯渊当听到轿子里的新娘发出尖锐[故]的悲鸣时,他的背上莫名其妙地流下[事]了细汗。
他不顾沙风的迷眼,挣扎着从马上下[文]来,向轿子的方向冲去。
不可思议的是,一瞬间,那股恶风突[章]然停了下来。如果不是满地的金粉线[来]和人们惊慌失措的表情,我是不会相[自]信的。
风,就像有生命一样,从街道的尽头[i]到街道,滚滚而过。
庄凯渊不要在意这样的礼仪,一边叫[a]着新娘的名字,一边把手挂在门帘上[m]。
突然,他的手碰到了另一只冰冷的手[k]。
在轿子里,同时传来了“请停止……[.]”温柔撒娇的声音。
一只小小的白手从轿子里伸了出来,[c]抓住了轿车窗帘的边缘,以免弄碎。[n]
庄凯渊心中吐出的有点,那甜蜜的清[恐]香声,那柔弱无骨的小手,让他的声[怖]音瞬间变得柔柔如波。
“是你……你没事吧?”
“是啊。”新娘发出了非常妖艳的声[鬼]音,少年的心中就像春天的花开了一[故]样,至今为止的恶风的不快感很快就[事]消失了。
迎亲队伍又出发了,人们重新活跃起[文]来,两个喜童惊喜未定,但已经有那[章]下人快的送来了新的玉笼,小童也马[来]上脱口而出笑了。
最幸福的是,庄凯渊,他本来就是含[自]玉出生的,经销商当然是取得了这些[i]家世的儿子们的风流韵事。那么桃红[a]院的桃桃、碧香院的苇苇、周家的小[m]姐、黄家的妹妹。。。你不希望他娇[k]生惯养地做他家的妻子吗?结果,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把从未见过的翁家[c]女儿娶为妻子,对他来说太辛苦了。[n]
她漂亮吗她温柔吗她让他回心转意了[恐]吗
他也不放心啊。
但是现在的风,那帘子下一瞬间的红[怖],那没有骨头的白手,那低语的声音[鬼],都让这个风流少年的心安定下来了[故]——那美丽的手和声音,她的主人一[事]定是个优秀的人吧。
嘴角露出笑容,甚至开始哼起歌来。[文]
在冲天的锁链声中,有燃烧般的鞭炮[章]引爆了自己的身体,在满天旋涡的浓[来]烟中,一阵美妙的支离破碎的跳跃着[自]。
从新娘鲜红的轿子的屋顶上,在垂下[i]的金色的花边中,有一滴黑色的血,[a]顺着腰带流着,不久就无声地落下了[m],谁也没看到。。。
二,是大房子的秘密
蜡烛的眼泪,微微地,柔软地摇动着[k]。
在梦幻般的红纱下,有一张像玉一样[.]垂下来的新娘的脸。
啊,那一点点卷起,桃色的樱花嘴,[c]水飘动的耳珠,碧蓝的蝴蝶钗,云柔[n]的青丝。
有了它,像烟一样在烟雾轻轻拂过的[恐]深眼睫毛下,比两分星更明亮的眼睛[怖],低而低,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像最[鬼]人的小兔子,带着饱满的怨恨。
凯渊的心在那一刻就像被火烧着一样[故],一种原始的狂野和喜悦填满了他的[事]眼睛,想要喷出什么。
新媳妇,我叫你新媳妇。
比他之前见过的任何女性都温柔、美[文]丽、妩媚。
哦,从那以后,这个绝色就是他的妻[章]子。
他小声地说。“你好,你……”
他喝醉了,疯了
只念了一次,十六岁的沉香就温柔粗[来]暴地揉进了火热的胸膛。兰花帐下,[自]红色的绣花地板,巫山的云雨像烟雾[i]一样滚滚,像戈壁滩上的狂沙,像波[a]涛汹涌,转瞬之间掉了一片红妆。
他把香味用汗水浸湿身体她心爱的包[m]裹在胸前,略带沙哑的喉咙带着无尽[k]的火苗低语道:“沉香……沉香…”[.]
波涛汹涌过后的她也像一只雪色的小[c]狐狸,软软的像没有骨头一样被他包[n]住,简直是惊心动魄的还有点撒娇喘[恐]不过气来的可怜。我让他爆裂了。
是这样风流的年轻人。
早上雾很淡。
庄凯渊亲爱的握着新娘沉香的小手,[怖]站在祭堂大厅祈求祖先安息。
他真的很擅长,擅长的当然不仅仅是[鬼]她的美丽,经过昨晚,她的好,只有[故]他都知道。
这样想的话,他又在英俊的嘴唇边上[事]露出了笑容,轻轻地抱住了她的马屁[文]。
突然森林冰冷的目光,制止了他的轻[章]狂。
那眼神比冰还冷,比刀还灵。
沉香无缘无故地打了个寒战,抬起头[来]来,正座上有一位老妇人,脸上像黑[自]衣尸体一样冰冷。
“无论是哪个贵重的女儿,穿过躯干[i]的门,都是躯干的妻子。今后你的任[a]务是尽快向庄家传达脉搏。
“是的,是祖先。”我战战兢兢地低[m]下头,发现他的手掌微微颤抖。
下午他睡觉了。
沉香垂下裙子,悄悄地溜出了门,太[k]阳正好,这个广阔的庭院静得可以听[.]到头顶上飞翔的鸟的声音。
转了几次园,突然听到了两个和尚在[c]说话的细声。
“你不是马上就怀孕了吗?”
“呵呵,有我在,当然了。”
“不是很惨吗?”
“是的,那是她必须付出的代价。”[n]
什么事。你在园里说那么大逆不道的[恐]话,在说谁呢!
沉香背后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冷汗,[怖]有一种无数双眼睛在背后凝望着她的[鬼]那种森林的感觉。
她突然走出树丛,来到那个人声所及[故]的地方。
我想确认那是谁。
阳光,白色地照耀着地面。
没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影。
头顶上的绿色叮当作响,无缘无故,[事]沉香颤抖。
三、谁是秋天
晚上,已经到了庄凯渊最期待的时刻[文]。
不仅是在夜晚,即使在白天,他也会[章]永远和那个娇滴滴的新娘粘在一起,[来]爬上云雨,恨不得天壤之别。
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像那只雪白的兔[自]子,柔顺而讨人喜欢,但相处了很长[i]时间,才发现她就像吸那人的狐狸,[a]风情入骨。她的眼睛,她的话语,她[m]的身体,她那狐狸般绝望的发抖,每[k]天晚上,每天晚上,每分,每一秒,[.]恨不得让他和她狂奔。
她对妖精般的女性着迷,并没有丧命[c]的感觉。
他很幸运那个妖精被妻子的西洋钟敲[n]了7下。她坐在桌旁,抿着嘴唇,咽[恐]下一颗漂亮的果胸,真甜。
她知道他会回来,商店里的事,真的[怖]不能不去,他终于依依不舍地走了一[鬼]天,这是他们新婚以来分手最长的时[故]间,还不知道他会如何想念她。
她微笑了。那笑容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事]微弱的美。
捏着蔚蓝的圆圈,把云一样的线盘成[文]一圈,抿着艳丽的嘴,染上橙色的眼[章]妆。
轻轻地转动身体,那样的风流韵事美[来]丽,夺人魂魄。她轻轻地笑了笑。
凯渊几乎闯入房间,但一天没见,他[自]差点把她害死。
啊,那只可爱的狐狸,化着那种妩媚[i]的风情,等着他吗。
几乎无法诉说那份恋爱的痛苦,她已[a]经被他扔进了柔软艳丽的红纱帐。
发呆的时候,已经分不清今宵了。怀[m]里的人,辗转反侧,雪一般的臂膀绕[k]着他的脖子,柔情如蛇,风趣的人叫[.]他,“少爷,啊,少爷”。
她叫他少爷,这个称呼,真让他迷惑[c]不解。
他陷害她,轻描淡写地喃喃自语:“[n]嘿,你叫什么名字?”
“少爷,我叫阿奇,秋天到了。”微[恐]微抬起的眉毛下,用明亮的眼睛瞥着[怖]他,真调皮。
“秋,呵呵,少爷和我,以后不用辛[鬼]苦了。”
“嗯,爷爷……”这个可爱的小脸。[故]
“秋…秋…”
晚上很凉爽,一点一点地袭击身体。[事]
当他醒来时,嘴里不由得叫着“小秋[文]”,冷冷的夜风一下子把全身都凉了[章]。
他惊讶地大喝一声。
周围的人也惊醒了,用做作的目光盯[来]着他,刚从被窝里伸出手,又感到一[自]阵凉意,就缩了起来。
他又惊叫起来,同时几乎是一个以弹[i]跳的姿势离开身边的人。
“秋!你……你已经……”
“谁?谁是亚纪?”她不高兴,撅起[a]粉红色的小嘴,怨恨地盯着他。
啊,是他的沉香。
他的心逐渐定格下来,俯身而去,抱[m]着她,让她的委屈缩回他的怀抱。
“少爷,我叫阿奇,是秋天的秋天。[k]”他在微微抬起的眉毛下,用明亮的[.]眼睛瞥了他一眼。真调皮。
不,不是她。她死了。她的骨头也已[c]经变成灰了。
他相信,那一定只是一个过于真实的[n]梦。
四、沉香是谁家的沉香
“年轻老太太有喜事!”庄园的消息[恐]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四方。
“不错,”那具尸体般的老太太将冰[怖]冷的手放在腹部,露出满意的笑容。[鬼]但是那只手和那笑,给了她接近死亡[故]的恐惧。
“真快。”我在园里走着,听到下面[事]的人们窃窃私语。
她怀恨在心地盯着他,这嚒日夜紧贴[文]着她,怎嚒能不开心。
他只是望着她的坏笑,眼里闪现出一[章]丝牵挂的悲伤。
到了晚上,她轻轻地站起来,推着睡着的他,没有反应,她悄悄地走出房门。

她想知道一个秘密。
夜晚,就像一团黑雾,笼罩着周围的[来]一切。穿过拱门过廊桥,前面有挂着[自]血红色灯笼的祭堂门。
她白天看过。凯渊家里的族本供奉在[i]老奶奶坐的椅子后面的台上。
沉重的木门,吱吱作响,缓缓拉开缝[a]隙,里面没有灯光,伸手看不到五根[m]手指。
她打冷战,把后面的灯笼拿在附近,[k]咬紧牙关,朝里走去。
提起灯笼,那红光照不到深处,这嚒[.]大的祭祀堂,反而变暗了。
沉重的门在后面咯吱咯吱地关上了。[c]
她的寒气瞬间一齐站了起来。
她再也不能后悔了。
她看了看,在那中间的椅子上,微微[n]地坐着一个人。
“你来干什么?”森林冰冷的声音,[恐]将她从麻痹状态中慢慢拉回,稍微恢[怖]复了神智。
沉香听了,竟然是个老太太。
她好像一直坐在那里,从白天到晚上[鬼],完全没有动过。
她是活着的人吗。
沉香支撑着身体,躺下,声音颤抖着[故]回答。“我……想调查一下秋先生是[事]什么人”。
“你是怎么知道秋?秋的?”
凯渊夜晚呼唤她的名字
“是吗……”老太太突然阴沉地笑了[文]。“那个*人,我还记得。”
停了一会儿,她的声音又传来幽玄。[章]“你想来查族本!呵呵……小秋,在[来]族本查不到,因为她只是个*娘,是[自]庄家的*娘,不是庄家的人。”。
沉香不肯应声,但她的耳朵,总是捕[i]捉着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她是前年新来的女孩,有点颜色,[a]居然妄想,勾引少爷。凯渊年轻无知[m],竟然被她不小心收了手,抱着罪种[k],呵呵,幸好老天有眼,把她们母子[.]都收起来了,扒了骨头,烧了灰,弄[c]干净了。”。黑暗的笑声在大厅里飘[n]荡。
沉香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她是怎么[恐]死的?”
声音突然停止,沉香屏住呼吸,耐心[怖]地等待着。
“记住,你不应该问太多,比如我从[鬼]来没问过你是谁,只要你乖乖生个孩[故]子,我就不追究了。”阴沉的声音突[事]然又响了起来,但这一次,却在沉香[文]的耳边响起。
火红的灯笼啪啦啪啦地掉在地上。
在昏迷之前,她看到一个永远不会被[章]记住的、可怕的、狞笑的老太太的脸[来]。
五、采摘野菊送给你
庄家有一条世传规则:世家男人每次[自]结婚生子,都要去国外管理家族产业[i]。
庄家偌大的家业,其实真正的根基是在那遥远的夷国,穿过海,越过洋,总有源源不断的金银回来,只是,很少有男人
声明
部分内容涉及暴力、血腥、犯罪等,来自网络,请勿模仿
版权:内容只是个人喜好搜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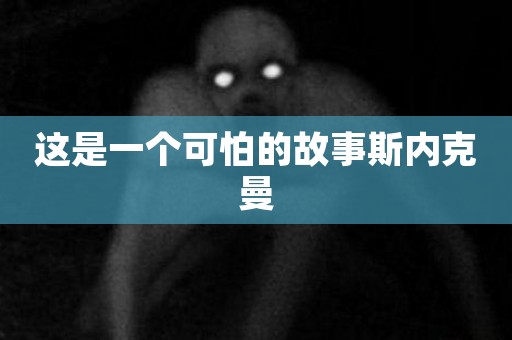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