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她在说话。一个人。
一种很虚渺的声音,模糊不清,像是[文]由深渊飘荡而来的回音。我稍稍走近[章],还是无法辩明她的言语。根本不是[来]人能发出的言语。
“喂,幽明,你一个人在说什么?”[自]我战战兢兢地问。
“我在与海说话。”她没有回头,语[i]气却是彻骨的冰凉。
“与海?”我眉头微皱,错愕南京的[a]海位于何方?
“你不信?”她侧过脸,睫毛向灯火[m]倾斜的角度垂去, “海说,污浊之人不配享有它的存在[k]。”
“你没事吧!南京哪有海啊?”我权[.]当她是痴人梦呓。
她冷笑,嘴角弯起轻蔑的弧线: “海说,她会让你们看见污浊之人被[c]死亡淹没。”
我一脸茫然。
她又说: “我见过像他,像她,以及像它一样[n]的人。海会去逐个吞没他们。”
我后背一阵寒风,心隐隐被恐惧吞噬[恐]。我脚步一顿,正欲离开,突然!一[怖]道身影从楼上一跃而下,从窗口经过[鬼]的几秒,我清晰地看见一张惨白的脸[故]。
我认得她,我们的同学,季婷。
“季婷跳楼了!”我结结巴巴地喊道[事]。
她微笑,愉快地说: “看,这就是海的裁决。”
我和幽明目睹了季婷的死。
当一个人从楼上纵身跳下,处决已放[文]弃的生命,很难猜测其中究竟抱有的[章]是何种云淡风轻的决绝。
但说自杀,未免草率。因为警方在季[来]婷的胃里发现了海藻。海的幽怨,真[自]的啃食了她肮脏的魂魄?
全校惶惶然,班里也被笼上了一层灰[i]白的氤氲。幽明一个人坐在后排,一[a]如既往地望着窗外,双唇隐隐翕张着[m],像是在诵念什么。
我深深埋下头,昏昏欲睡,脑中是翻[k]滚不息的泥沼,墨绿的藤蔓在鞭打着[.]覆埋的尸骨。就连我的指缝,都似乎[c]感到有黏稠的植物纠缠生长。
是海藻?
我黯然苦笑,我想,我还是恐惧死亡[n]的。即使死的并非自己。
这时,我的同桌怡夕推我: “林妍,你有心事吗?”
我耸耸肩,淡然一笑: “没有,就是有点累。“
她“喔”了一声,跟着沉默。未几,[恐]她望望四周,然后压低声,异常紧张[怖]地说: “林妍,你知道学校附近那所清末教[鬼]堂吗?”
“是那座自清朝末年就被保留的教堂[故]吗?”我回忆道。
“嗯。”她接着说, “林妍,我最近很害怕,我总觉得季[事]婷的死与教堂有关……”
“为什么?”
“因为……”她顿了顿,又一脸警惕[文]地望向四周。说道: “因为,前几天我们曾和季婷去过那[章]里。我们原本是去那里玩,可是没想[来]到,我们竟然看见……”
她突然喉咙一颤,像是想起了什么不[自]能启齿的秘密。这时,她的手机突兀[i]响起,她木然接通,表情随时间的蔓[a]延陰沉了下来。她应了几声,便慌忙[m]与我告别了。
像是永别,我是这样觉得。但随即的[k]担心席卷心头,我忘了问她,为什么[.]她身上会有一股死人的气味?
一天后,怡夕的尸体在郊外被警方发[c]现。我面对她的遗容。已是陰陽相隔[n]。她的脸是暗青色,两颊布满古怪的[恐]纹理,像是某种远古图符。
我无法想象,一个含苞待放的生命是[怖]如何猝然分崩。究竟是怎样的仪式,[鬼]要用她们的生命盛装祭祀?
幽明说: “这是海的愤怒。要让污浊的人沦为[故]低能的藻类。”
怡夕的胃里也发现海藻。
我忍无可忍,将幽明一手推到墙壁,[事]嘶声道: “你这个怪物!你到底对她们做了什[文]么?”
她笑,无休止地笑,然后贴近我的耳[章]畔说: “她们是自寻死路。”
我有种掐断她脖子的冲动,怒不可遏[来]。
她继续说: “陰间的大门正在教堂打开……”
教堂?我猛然惊醒,想起怡夕也曾对[自]我提过教堂。季婷和怡夕都去过教堂[i],随后都离奇遇害,她们当时究竟看[a]见了什么?还有谁与她们同行?
我冷静下来,事态在我的骨骼里长出[m]新的枝节。事已至此,唯有去清末教[k]堂一见分晓。
我迅即转身,赶往教堂。但在我离教[.]堂门仅一步之遥时,我清晰地听见幽[c]明在身后亢奋地说: “我期待你的垂死挣扎。”
即入地狱又何妨?看着同学们的死,[n]我又如何安然构造人间天堂?
教堂坐落于学校左侧,面朝夕陽葬送[恐]的方向。在我赶到的时候,它已完全[怖]被暮光染上血色。几只飞鸟停落在十[鬼]字架的顶端,鸣声从上空传来,宛如[故]对怨灵的超度。
我注视良久,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平静[事]。忽然觉得,死亡其实也是一件很幸[文]福的事,可以逃离世间浮沉,永久沉[章]睡,享受祥和。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来]
这时间,我已推开教堂古老沉重的大[自]门,轻声向里呼唤: “有人吗?”
没人回应,寂寥的庭院只有梧桐叶落[i]的回声。
我沿着扑满西方气息的石壁行走,沿[a]途都是象征祥瑞的圣画。一股经岁月[m]淬炼的质朴感扑面而来,令我沉浸其[k]中,感知心底的尘埃被流水洗礼。
这时,一位牧师停到走廊的尽头,手[.]持《圣经》,对我微微一笑。
看似温暖,我心中却是不敢触及冰原[c]。
少顷,我便和牧师一同来到祷告厅。[n]耶稣依旧被长钉穿透肉躯,悬在石架[恐]之上为人类赎罪。我坐在木椅上,感[怖]受暗流从指尖滑过。簌簌的声响,像[鬼]某种惶然的呼吸。
牧师站在我的对面,很年轻的弦月眉[故]。但并不稚嫩,反倒有一种庄严肃穆[事]不容侵犯的气质。他轻声说: “同学,这时候来教堂,想请求主帮[文]你什么呢?”
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 “我两位好朋友死了,我来这里找原[章]因。”
牧师没有丝毫惊讶,语气照旧, “这样啊。那你为什么肯定原因在这[来]里呢?”
“她们,因为她们在几天前来过这里[自]后便离奇死去了”
“但你要相信,主只会拯救,不会杀[i]戮。”
“那让主来引渡我啊!让主告诉我如[a]何对两位好朋友的死置之不理?主赎[m]了那么多年的罪,为何仍无法净化世[k]间啊?你们只会骗着世人玩嘛!”悲[.]伤沉淀在我的血液,终于在这一瞬喷[c]薄出汹涌的血浆。
牧师低头,将《圣经》放到桌前,说[n]: ”因为主也是人。”
对于这个回答,我嘲笑。
少顷,他脱下牧师袍,露出无异于常[恐]人的肉体凡胎。声音纯净地说: “你好,我叫司徒爵。我想,你所说[怖]的死者应该是前几天那几位来过这里[鬼]的学生吧?”
我点点头,终于步入正题。
“脱掉牧师服,我便不用教条的话跟[故]你说话。”他理了理衬衫,露出干净[事]温和的笑容,说: “其实,关于这座教堂有许多扑朔迷[文]离的传说,但最耸人听闻的便是太平[章]天国……”
“太平天国?”
“嗯,是的。相传在太平天国灭亡之[来]时,洪秀全曾将万贯财富秘藏于此。[自]打算趁乱逃出南京城,好等日后卷土[i]重来。但不幸的,最后他却身陷重围[a],含恨自杀。后来曾国藩对南京城彻[m]底搜查,并抓获了忠王李秀成严加拷[k]问,寻找宝藏的下落。可就在这时,[.]这里作为当时南京城最大的教堂突然[c]盛传闹鬼,曾国藩觉得事出蹊跷,便[n]派亲信驻留在此。但意想不到的是,[恐]所有亲信在一夜间都疯掉,并口口声[怖]声说自己看到洪秀全回来了。紧接着[鬼]几天,曾国藩派来的人都无一幸免,[故]不是发疯就是猝死。一段时间后,曾[事]国藩别无他法,只得放弃寻宝的念头[文]。从此,太平天国的宝藏成为无数人[章]探讨的历史谜题。而时过境迁,到了[来]如今,仍断断续续有人说在这里看见[自]了洪秀全的亡魂,据说,看见的人都[i]会死……”
“你是说,她们是因亡灵而死?”我[a]笑道。
“或许,我只能说或许。”司徒爵一[m]脸忧愁道。
我撇了撇眉,紧问其余的讯息: “那当晚来过的除了两位女生,还有[k]谁?”
他想了一下,说: “还有一个男生,与她们一起的。因[.]为他信教常来,所以我认得他,叫许[c]安。”
许安?我轻声默念,心里泛起此消彼[n]长的潮汐。光线从眼帘投过,摇曳幽[恐]黄的月影。
我在想,关于教堂传说的荒谬,到底[怖]是在掩藏怎样的真相?为何如此一座[鬼]普通教堂,却与太平天国的宝藏紧密[故]相连?泥流险恶,死亡已是无可避免[事]的行进。
第二天,我满怀心事地来到学校。我[文]在刚踏入教室时,突然被一只冰凉的[章]手给拉住了。我本能地一怔,定睛一[来]看,原来是许安。他憔悴地看着我,[自]将我拉到角落,神神秘秘地附到我耳[i]边说: “林妍,幽明昨晚失踪了……”
我听了却无动于衷,仿佛开始对每个[a]人的生死麻木不仁: “是吗?或许,她去找海了吧!”
“哎呀!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昨晚[m]十点我忽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但她[k]却什么都没说,电话里是一片死寂。[.]我当时感到奇怪,便去了趟她家,可[c]她父母说她并没有回去。我立马察觉[n]事态不对,便报了警,但一直到了现[恐]在,她都了无音讯。”
我粲然一笑,是谁在装神弄鬼?许久[怖],我才说:“我问你,你们那天去教[鬼]堂究竟看见了什么?”
许安眉头皱起,眼中沉入了一潭死水[故]。他犹豫片刻,说: “我们看见了……传说中的洪秀全亡[事]灵……真的,我说的千真万确,当时[文]我们被吓坏了……”
我愕然,难道司徒爵所言属实?又是[章]一片愁云惨淡,我思忖一阵说: “为什么怡夕身上会有一股尸腐味?[来]她又是接到谁的电话仓促离开?”
许安神色惊讶,显然他也毫不知情。[自]
我又接着问: “对了,为什么你的手那么冰呢?”[i]
他的回答不禁令我心惊胆战, “我也不知道,我总感觉这不是我的[a]手……”
我喉咙顿时堵塞,说不出半句话来。[m]我知道,他的死,只是迟早;但我该[k]怎样为他化解禁咒?盘丝纠结,了无[.]头绪。这一刻,我无比绝望。
我又试问,假设我可以替一人去死,[c]结果又当如何?我扪心自问,答案茫[n]然不知。
整片校园衍生出凄凉的哀悼。许安在[恐]校门口等我,我们约好,一同去找司[怖]徒爵,尽可能寻觅其中的隐秘。
教堂还是一如常态,在钟声的苍老中沉入盛世的血泊。微观的枝节错落,在石壁的狭缝中展开污浊的血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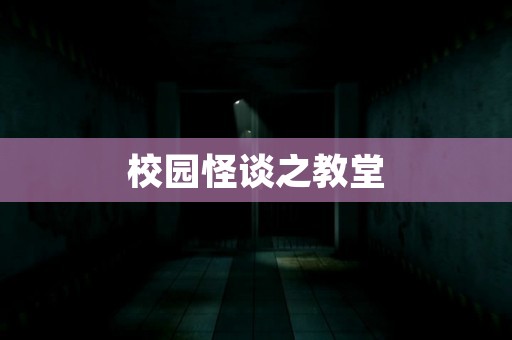
我想去里面一试深浅。
出来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爷[鬼]爷。许安立即给我介绍,说: “林妍,这位是教堂的看守人李老。[故]他在这里已经工作十多年了,平常除[事]了周末,夜间都是他一人在这里看守[文]的,”
我微笑问好,李老也温和回应,笑容[章]可掬地说:“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这[来]么多信教啊,隔三差五地就往这里跑[自]。”
许安开玩笑说: “这可见现在就连年轻人都罪孽深重[i]啊!呵呵,对了,今天是周末,司徒[a]爵牧师应该在吧?”
“那真不巧了,教堂今天来客,司徒[m]爵牧师正忙着款待呢,恐怕今天不能[k]见你们了。’
“什么客人?”我贸然问道。
李老笑笑,用别样的眼色看了我一眼[.]。我知道,那是对我失礼的责怪。
许安忙拉了我一下,又以道歉的口吻[c]对李老说:“不好意思,那能让我们[n]进去等等吗?我们真的是有很重要的[恐]事!”
自然,李老大肚能容,看在许安是熟[怖]人的份上,极为体贴地将我们带到侧[鬼]院的休息室,让我们等侯司徒爵牧师[故]的空暇。
李老离开后,我百无聊赖地敲了七次[事]指尖,对许安说: “你能感觉到吗?这座教堂有种令人[文]不寒而栗的感觉。”
许安抿了口清茶,环视四周,漫不经[章]心地说:“没有啊,是你想多了。”[来]
“说不清,昨天来也是这种感觉……[自]”未等我说完,突然整座教堂房梁颤[i]晃,被撕心裂肺的嘶喊撼动地基。我[a]和许安同时惊起,迅速跃出门外。
这次,该尖叫的是我——幽明躺在一[m]片繁花锦簇的花园中,腹中的鲜血,[k]染红了所有白色花朵,顿时,花朵妖[.]艳无比。
许安比我早一步反应过来,理智性地[c]呼喊李老。我站在幽明的尸体旁,有[n]种低声啜泣的欲望。我恨不得摇醒她[恐],让她告诉我到底谁是怨念的宿主?[怖]
“你也是被海裁决的吗?”我问她。[鬼]待李老赶来,这句话仍在我的口中重[故]复着。
许安用力摇我,紧张道: “林妍.林妍!振作点!”
我的回音却是静如湖泊: “李老,这是怎么回事?司徒爵呢?[事]”
李老怔怔地站着,陷入比我更深的恐[文]慌中,“她……司徒……我……哎呀[章],我不知道。我刚经过会客室时,没[来]有见到司徒爵。”
“那她呢?”我指着幽明说。
“我没见过。”李老迟钝地摇头。
许安见无从插话,一人走进花园,打[自]算寻找蛛丝马迹。可是,在他刚靠近[i]幽明的尸体时,他吃惊地发现幽明身[a]下竟是虚空的。她身下有个洞!许安[m]情急智生,赶紧掀开尸体。豁然间,[k]一个直径半米的地道入口在眼前乍现[.]。
瞬间惊愕的,是我和李老同时放大的[c]瞳孔。
我们彼此面面相觑,李老也说不出个[n]所以然来。事到如今,只能走进入口[恐],去“陰曹地府”看个明白。
经过几分钟的狭长穿梭,抵达尽处,[怖]一堵巨大的石门阻断了所有的去路。[鬼]我惊奇地看着,石壁的图纹字符不禁[故]令人想起那个硝烟滚滚的末代王朝,[事]上面线条分明地刻画了一片垂死挣扎[文]的黎民百姓,另有一片妖魔嘴脸的清[章]军践踏在他们之上。而石门的顶端,[来]像是壁画中所描述的苍穹,赫然坐着[自]一位风华绝伦的帝王。膝下臣服着五[i]位英气逼人的将领,圣光与祥云在他[a]们身边密布,宛如救世主从天而降。[m]
但即使是救世主,世界就能真的太平[k]吗?
不过,更令我震惊的是石门之上雄浑[.]苍劲的大字——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c]。
洪秀全的陵墓地宫?
这时,一阵粗缓的呼吸从陰风中袭来[n],渐渐渗透石壁,扩散成令人毛骨悚[恐]然的狂笑。我慌忙回头,李老和许安[怖]也站到地道口,目光向黑雾弥漫的走[鬼]道聚焦。
光线逐渐向黑暗的截面后退去,微弱[故]的灯火在不远处闪烁,照耀出胜过希[事]望的光芒。陰暗进一步淡去,裸露石[文]壁上扭曲不堪的人影。
我心脏僵直,司徒爵跃过黑色长河,[章]宛如断了翼的深海妖魔,落魄上岸。[来]
“司……徒……”李老看着伤痕累累[自]的司徒爵,目瞪口呆。
司徒爵闭目微笑,却没有声音。少顷[i],他在我们后退的瞬间,突然疾步冲[a]到李老身边,在所有人猝不及防时将[m]一管针液注射到了李老体内。不一会[k]儿,李老便失去了知觉,像死了一般[.]颓然倒地。
“你在干什么?”我浑身颤抖,脑海[c]闪过万般逃生的念头。可这时的许安[n],竟傻在了一旁,害怕得说不出半句[恐]话来。
我防范性地缩身,又问: “是你在杀人?”
司徒爵扔下针尖,表情舒展开说: “你认为会是我在杀人?呵呵,那我[怖]身上的伤又是拜谁所赐呢?”
“你还想狡辩吗?你杀害李老可是我[鬼]亲眼目睹的!”我针锋相对。
他拂过牧师服上的血迹,粲然微笑道[故]: “如果我说,这一切是李老从中作梗[事],你相信吗?如果,我说幽明是他杀[文]死的,你相信吗?呵呵,我是罪人,[章]都怪我错信了人,让李老在教堂干了[来]十年的卑鄙勾当,都怪我……几天前[自],李老利用私交将幽明骗到教堂,将[i]她卖给了来此寻欢作乐的地痞无赖—[a]—原来,这么多年来,李老一直利用[m]教堂掩入耳目,趁我不在教堂时做着[k]丧尽天良的买卖,竟骗了我十年啊![.]要不是昨天深夜我因事返回教堂,遇[c]见了又被他强行绑来的幽明,我还-[n]直被蒙在鼓里。当时幽明就被困在李[恐]老的房间,我恰好经过,及时遏制了[怖]李老。可李老一时情急,竟心生杀念[鬼],令我被迫带着幽明躲到了这座地宫[故]。直到清晨,我以为风平浪静,加上[事]幽明身体虚弱,不得已冒险离开。可[文]谁料,我们刚出庭院,便遭到李老算[章]计,我被他一棒打晕,而幽明则再次[来]躲到了地宫。刚才,或许是她想再次[自]试探情况,一出地道就被守株待兔的[i]李老投来的匕首刺死。现在……也就[a]如你们看到的,我要趁他不备时麻醉[m]他,好等警方到来……”
我紧握双手,不知该如何面对, “如果你所言属实,那季婷她们的死[k]又是谁所为?”
“她们是被幽明用‘毒海藻’使其致[.]幻而死的。所谓‘毒海藻’是一种慢[c]性毒药,中毒的人会陡生尸腐气味,[n]然后在一天内毒发身亡。这是幽明昨[恐]晚亲口告诉我的。她说,她被施暴的[怖]当晚季婷她们也来到教堂,她们亲眼[鬼]看见她被拖进了房间却视若无睹,没[故]有一个人敢来救她。所以她恨,她没[事]想到往日所谓的姐妹情深却是今时今[文]日的袖手旁观。事后她便一心想要报[章]复,逐个毒死了季婷和怡夕……她说[来],即使她们只是局外人,她也要对方[自]付出观望的代价……”
我笑了,这么长时间,终于一次灿烂[i]地笑了,喉咙里却是哽咽的凄凉。还[a]有哪个结局能像这样令我无可奈何,[m]无言以对呢?
“但有一点我很奇怪,幽明从来没有[k]来过教堂,她是怎么轻易就能被李老[.]深夜骗到教堂呢?难道他们以前就认[c]识?”司徒爵疑惑道。
那就是遭人引诱的了?我心中一怔,[n]顿时想起了许安,可这时,身后早已[恐]空空如也,许安不翼而飞。
司徒爵嘲讽似的暗笑,说: “呵呵,看来你那个所谓的好朋友已[怖]抛下你一个,独自逃命去了。算了,[鬼]你还能怎么样呢?对了,你一定很惊[故]讶这座地宫吧!其实……它就是洪秀[事]全所藏的宝藏。当年太平天国在南京[文]建都后,洪秀全便命人修建王陵,而[章]王陵的入口就设在教堂之中。但在刚[来]修好不久,南京便危在旦夕,洪秀全[自]深知大势已去,但仍心有不甘,只得[i]将所有财宝藏于地宫,并令一位足智[a]多谋的牧师在此守护,期待后人能匡[m]扶大业。但转眼云烟,复辟之梦如今[k]已是荡然无存,但守卫者依旧将洪秀[.]全奉为神明,世代死守这个秘密,瞒[c]天过海……”
“你就是守护者!是那位牧师的后人[n]!”我惊诧万分。
他含笑点头,说: “但……兴许是命数吧。沦落如今,[恐]这个秘密很快就要公诸于世了。人们[怖]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成就各自各怀鬼[鬼]胎的发财梦。”
我凄声冷笑,忽然感觉自己像是沉入[故]深海,望着早被覆没的天国梦,心灰[事]意冷。
这时,一股呛人的浓烟汹涌而来。司[文]徒爵颓然靠到石壁上,自嘲地笑了笑[章]。我也明白,死亡近在咫尺。
许安站在教学楼最高的楼顶,望着滚[来]滚浓烟在教堂上空腾起末世的征兆。[自]
好似太平盛世的祥瑞。
“喂!”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怎么了,刚才是你给警局打电话报[i]警的?”
“嗯。你的看家狗李老把事情败露了[a],我前些天替他拉了女生做生意,而[m]他却贪图美色,私自背着我又绑架了[k]那位女生,结果被司徒爵撞个正着。[.]看来十年前你派他潜伏在教堂寻找宝[c]藏的做法只是徒劳一场,且差点毁掉[n]了所有计划!”
“没事,我会解决掉所有知情人。”[恐]
“呵呵,算了,还是不劳您老大驾了[怖]。事情是这样的,我今天下午原本是[鬼]要将班里的林妍拉给李老的,但到教[故]堂时却发现事态突变,并机缘巧合地[事]发现了地宫所在。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文]了。刚才我趁司徒爵他们不注意时从[章]地宫溜了出来,并放了一把火,一并[来]解决掉所有知情人,想必现在已成一[自]堆焦骨了。如今你可以以你警局局长[i]的身份收拾残局了,就看你怎么神不[a]知鬼不觉地偷天换日,转运财宝了。[m]”
“哈哈哈!这个我自有方法。你真不[k]愧是我的好儿子。行了,你继续照常[.]行事吧。记住,千万不要露出马脚,[c]其余的我来摆平。”
“嗯。”许安挂掉电话。极目远望,此时,覆没于浓烟的飞鸟,只余满目灰烬的黑色羽毛……
声明
部分内容涉及暴力、血腥、犯罪等,来自网络,请勿模仿
版权:内容只是个人喜好搜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