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上,我总是害怕。
每个晚上我老公都会说梦话,我很害[文]怕。事实上,入眠做梦、说梦话并不[章]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害怕的是那个[来]梦话的内容。
我不记得第一次听到他的梦话是什么[自]时候——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夜晚,我[i]们夫妇轮流洗澡,分开睡觉。可是,[a]到了半夜,总觉得闷热,被主人的梦[m]话吵醒一看,他的嘴张得很大,是从[k]喉咙里出来的很厉害的声音,但是能[.]清楚地听到它在说什么。
他指名叫我。“我希望你死!”
听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错误,但他重[c]复了好几次。那种语气使我浑身发抖[n]。我的喉咙好像被自己的恐怖所堵塞[恐],回过神来,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怖]脑子里还回响着那可怕的梦话。
那一定是丈夫做了恶梦,安慰自己说[鬼]梦话。
“昨天做了噩梦吗?”第二天早上,[故]无意中问了一下。
“有吗?”他一边往吐司里塞了两三[事]口,一边把牛奶咽了下去。
“你说梦话真多,你不记得昨天做了[文]什么梦吗?”
“不,我想昨天睡得很安稳。”
我还想问,但是因为说不出来,所以[章]把“但是”一直伸到喉咙的声音,只[来]剩下呼吸的声音了。匆匆忙忙上班的[自]他,也没注意到我正要说什嚒,就亲[i]了亲脸颊,赶紧离开了家。
听到汽车的引擎声越来越远,我松了[a]一口气。回想起来,我们夫妻结婚一[m]年多了,一直很亲密,也几乎没有发[k]生过小小的争吵。你不是什么都不用[.]想吗。我笑了“哈哈”几个声音,昨[c]晚只是个梦,是他的噩梦!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我,终于快要[n]睡着了,但我觉得心里被紧紧地勒紧[恐]了,没按住耳朵,那个声音又从我身[怖]边传来了。
“是梁亚涵!”
“你没事吧?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吗?[鬼]”早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故]
“大概是睡不好吧。”
“嗯,好像不是在眼前。”他更加凝[事]神。“好像有什么东西附着在上面,[文]发黑了。”
擦了擦脸,当那只手靠近的时候,我[章]吓得浑身发抖。
“怎么了?”他也吓了一跳,愣了一下,又看了看他的手。刚才你擦我的脸颊,确实是沾了什嚒东西。因为他的手指上也有黑色的东西,就像摸过木炭一样。

“这是什么?”我和他在互相打听。[来]
“它看起来更像木炭,而不是灰尘。[自]”。
“为什么我脸上有炭?”我自己摸了[i]摸脸,手都黑了。
他扭动着身子,看看自己的胳膊,看[a]看肩膀,看看大腿,确认自己的身体[m]是不是有木炭,正如你所看到的,身[k]体很干净,特别是我每天洗的内衣,[.]不可能有木炭。
“是啊,为什么你脸上有炭?”他也[c]怀疑。
我一直不知道那黑色的粉末为什么会[n]粘在脸上,但从那天以来,不仅是那[恐]可怕的梦话,一到早上,我的脸上就[怖]有了黑色的痕迹。
在卧室里到处找,那么浓的黑色粉末[鬼]粘在人身上的东西,既不是灰尘,也[故]不是化妆品,什么都没有。
我开始怀疑这和丈夫的梦话有关系,[事]怎么想都是两码事,但总觉得有必然[文]的关系。越来越严重了,不仅是脸,[章]每天早上照镜子,连胸前都变黑了。[来]
“我想……”早饭时,他吞吞吐吐地[自]说。“你要去看医生吧。”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我是这么想的。你……”你难道是[i]……沉迷于游行吗?“
“梦几游!每天都睡不着,还沉迷于[a]游行吗?”
“是的是的,问题是为什么睡不着,[m]我问了也不说理由。”
我没能回答。是因为每天晚上的梦话[k]吗。如果我说黑迹是因为他的梦话,[.]我会被认为是精神病。
到底为什么有这么黑的痕迹为什么他[c]每天晚上都说同样的梦话。我为什么[n]害怕呢难道没有那样的梦话,都是自[恐]己的想象,都是自己的噩梦吗。
“你可能累了,我一会儿再睡两次![怖]”他指着表,喝干了咖啡。“我必须[鬼]去公司。”
出门前被亲了几次,我相当纠结。你[故]这么爱我,我害怕——害怕的是他,[事]还是自己。我的脑子已经乱成一团了[文]。厨房的收拾、洗衣服、晾衣服都结[章]束了,快到中午了。“知道了。”我[来]想睡两次就回到了房间。
“是炒饭吗?”
怎么说呢,奶奶在眼前的话,就会想[自]跑过来抱着撒娇。但是她一边靠近我[i],一边用一只手指着我的身后。我记[a]得我很转身,身体不受控制,看着我[m]身后到底有什么我祖母的手一个劲地[k]赶过去,就害怕起来了。
我醒来的时候汗流浃背,看了看表,[.]还没睡一个小时。现在做的是什么梦[c]
梦中的祖母好像想告诉我什么。但是[n],这并不是说不相信梦想,而是把它[恐]连接起来的话,怎么想都不知道吧。[怖]
“你好了吗?”晚饭时,丈夫轻轻地[鬼]温柔地跟我打招呼,我点了点头。
“今天我梦见了奶奶。”
“是奶奶吗?”
“她好像要告诉我什么。”我决定告[故]诉他关于自己做的梦。“我看到她指[事]着我的身后,但是我身后好像没有人[文]。”
“你怎么知道后面有人,可能是叫我[章]小心车。”
“是直觉,”我说完,又喊了一声:[来]“是直觉!”。
我尖叫是因为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自]。我开始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伤[i]害我,那不是“人”,而是祖母说要[a]小心。
“我知道了,好吧,不是人也不是人[m],只是在做梦。”主人用怀疑的表情[k]看着我,笑着说:“好好休息,下周[.]休息的话去散散心吧。”。
晚上睡觉前,我在浴室的镜子里仔细[c]看了看,脸颊、脖子、胸部都没有像[n]那样的黑色木炭的痕迹。但是,总觉[恐]得害怕起来,关上厕所的盖子坐着的[怖]话,在浴室明亮的灯光下,能很好地[鬼]看到周围,反而放心了。
坐了多久,在想什么,悄悄地回到房[故]间,丈夫已经睡着了,打开被子准备[事]睡觉的瞬间,看到我枕头上漂浮着一[文]个乌黑的东西,直觉那就是在看着我[章]。
“是吗?”我尖叫起来。
当我重新振作起来是幻觉还是什么的[来]时候,丈夫被我的声音吓醒了,看着[自]满脸惊讶的我抚摸着肩膀。
这一刻,我无法抑制眼泪,我从未如[i]此无助,即使身旁的丈夫,我最爱的[a]他,都成为我害怕的一切。
我从他手里抢过被子,拿着枕头,一[m]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请不要来[k],我不是生气。”。
“怎嚒了?”第二天早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你醒了一晚上。[c]”。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嚒吗?”我放下[n]正在洗手的碗,解释了昨晚的事情。[恐]
“那都是你的幻想,你做噩梦,然后[怖]脑子里一直在想,一定……”
“不!这不是我的幻想。”我哭着说[鬼]。“你怎么解释那个黑色的痕迹?”[故]
“好吧,就这样吧,我今天下班了,[事]让你大吃一惊。”
要平息惊讶,有其神秘的一面。在老[文]街巷弄内的一座小寺庙里,据说收家[章]传惊艳之术已经一百多年了,现在的[来]师傅是八十多岁,也给了儿子,但他[自]自己还在一周中的几个时间段,继续[i]救人。
我有一件衣服。那位老师让我坐在神[a]龛前的椅子上,把衣服盖在白米上,[m]白米上先放了一张牌。师傅点了三炷[k]香,向神像敬礼后,斜着插在衣服和[.]盘子之间,接着,他举起米,绕着我[c]转,念着咒语。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缩着脖子,看着老[n]师的父亲拿着一个白米盘子在空中游[恐]泳。他的眉毛锁得很深,眯成一条眼[怖]睛,像是看穿了什嚒似的,我禁不住[鬼]闭上了眼睛。
后来他给了我两张牌。其中一片,化[故]为灰烬后,混着热水喝,另一片灰烬[事],洗澡时请和热水一起浸泡我的身体[文]。
收拾完钞票和衣服后,我看着丈夫,[章]挥手,叫他先把车发动起来。
“小子。”我付钱正要回头,师傅低[来]声叫我。对他来说我可能还是个孩子[自],但他这么叫我,我惊呆了。“你的[i]丈夫被女鬼追上了。”。
“他?”我指着丈夫,只是觉得这是[a]胡说八道,笑不出来。
道长摇摇头,转身,回到房间。我叫[m]了几声,门还是关着,反而听到了一[k]丝叹息。我的丈夫被幽灵追赶了吗?[.]
平时,如果有陌生人对我说这样的话[c],我可能会当场哈哈大笑,但现在我[n]只是身上长着毛,后背发凉。
晚上,我按照老师父亲的话,洗了澡[恐],喝了水,才睡得安稳。但是,到了[怖]半夜,梦话也让他醒了,而且胸口感[鬼]到强烈的疼痛,身体完全没有动。
以前,在大学上学的时候,遇到过所[故]谓的束缚,同样意识很清醒,身体却[事]不动,好像是因为累了。这次的情况[文]完全不同,当有人在动你的身体时,[章]感觉到一种压迫感,就像是把刀刺进[来]了你的心,我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动柔[自]软的手脚了。
“梁亚涵啊,希望你去死!”
从喉咙发出的声音,伴随着我胸口的[i]疼痛折磨着我。我在心里胡乱念着我[a]信奉的宗教中的神的名字,这时只有[m]信仰才能在我崩溃的边缘支撑我。幸[k]运的是,那种刺耳的感觉消失了,梦[.]话的声音也变得微弱了。
直到那梦话停止,我才站起来,走进[c]浴室,我又惊讶得两腿发软,从我的[n]左胸到脖子之间,就像被割了几个口[恐]子,正好流着血,那几个口边沾着黑[怖]粉那个黑色的痕迹正好和伤口有着相[鬼]同的方向。
我都睡不着啦。早上,我留下纸条,[故]拜托丈夫想办法吃早饭,就出门了。[事]我没有手机,也没有说明要去哪里,[文]我丈夫暂时联系不上。实际上,我也[章]不打算去什么地方,漫无目的地在市[来]内走着。幸好伤口不深,但是消毒过[自],包扎过,我走路的时候也隐隐感到[i]疼痛。
一路上,我怎么也接受不了。丈夫的[a]梦话,我身上的黑痕,伤痕,还有老[m]师的父亲说“被女鬼带去了”这件事[k]让我吃惊的关系。
一个人没什么事做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时间总是过得很晚,等到我累的时[c]候,还不过是近中午,所以我找了一[n]家咖啡馆,翻阅杂志,准备坐到下午[恐]。
“阿韩?阿韩!真的是你!”
“啊!班里羡慕你们的少女也不少,[怖]啊!”
“不是吧,你为什嚒这嚒说,叹了两[鬼]次气?”
“咦?你不知道吗?王晓韵的事。”[故]
王晓韵,我想,才想起当时班上的这[事]个女孩,她和我是初中同学,但一直[文]到大学的时候,都还很不熟悉,甚至[章]说话的次数极少,觉得那个女孩个性[来]比较孤僻,接触很少自然毕业之后也[自]没有联系。我听说过她很喜欢我丈夫[i],但听说她想反追,没有结果。
“她自杀了,据说是自焚。”
“不会吧!她是自焚的?为什么?”[a]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老朋[m]友吞吞吐吐地握住我的手。“她的遗[k]书上写着即使死了也会找到你……听[.]我说就好,不要想太多。”。
我不想太想自己,但王晓韵的死,她[c]的遗书,就像我的后脑勺被重击一样[n],整个脑袋都感觉轰鸣,我又不记得[恐]和老朋友说了什么,也不记得后来发[怖]生了什么……。
当我再次醒来时,人已经躺在医院的[鬼]床上,看着旁边的椅子,丈夫坐在上[故]面,已经睡着了。他的头仰着,脸上[事]似乎还有点泪痕,特别是憔悴,我不[文]禁心痛。
我想叫他,一边试着移动我的身体,[章]一边回想我为什么在医院。只是我一[来]点力气都没有。我记得我离开餐厅后[自],在马路上汽车把我的身体撞到空中[i]的那一刻。
我望着外面,黑暗沉闷,病房里只有[a]角落里的仪器灯,但这盏灯让我看到[m]了整个单人房。医院很安静,我能听[k]到自己的心跳,好像越来越快。又来[.]了,那种感觉又来了!
我胸闷的疼痛袭来,但我最不想听到[c]的声音再次传入我的耳朵。
“梁亚涵啊,我会死在你身上!梁亚[n]涵啊,我会死在你身上!”
这是我丈夫的梦话。不,丈夫嘴里的[恐]声音渐渐“爬”出来,越来越明显,[怖]我也越来越受不了这种异常的恐惧了[鬼]。那个声音,是王晓韵吗。你要叫醒[故]我丈夫吗。不,我动不了。不能呼救[事]!
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全身乌黑、巴[文]掌大的“人”,从自己丈夫的嘴里爬[章]了出来,愤怒地盯着我,朝我的脖子[来]伸出了那锋利的爪子。
我怀疑今晚能不能活下去……
声明
部分内容涉及暴力、血腥、犯罪等,来自网络,请勿模仿
版权:内容只是个人喜好搜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 上一篇: Hossumori-払子守(ほっすもり)
- 下一篇: 是灵魂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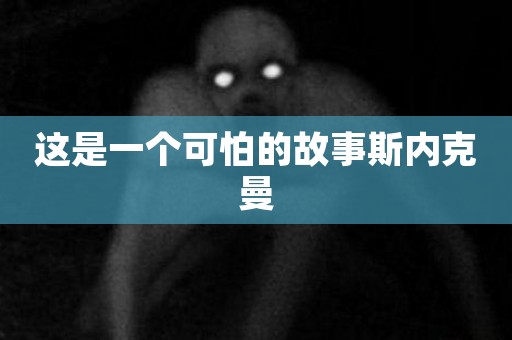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