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金融危机,妻子所在的矿井放了半年假,安心在家做饭,但日子过得很平静。一天突然,妻子接了同事的电话后,一脸不快。眼睛里流露出失望,间忽还有点害怕。
我追问了好几遍,老婆终于说出了原[文]委。矿山的选煤楼发生了事故。休息[章]后,检查工从10多米的高度摔下来[来],摔死啦。这样一来,风险抵押金和[自]安全奖都没有了。失去同事,心情郁[i]闷,人之常情,失去一些物质利益,[a]感到遗憾,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没有[m]什么可怕的吧。
我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的脸,想从那里[k]找到什么,但她的嘴反复说:“还是[.]在那里,还是在那里?”。
我问“在哪里?”。
“那个人死的地方,那里不只是死了[c]一个人,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妻[n]子直着眼睛,声音轻盈,“隔了几年[恐]才死,真可怕!”妻子的想法似乎完[怖]全回到了她洗球队的岁月。
妻子先是在洗煤厂工作,当时的工作[鬼]时间是三班倒,每隔两周换到下半场[故],下半场是恐怖的高发期。有妻子的[事]山丘上并不孤独,同时有三个人。包[文]括妻子在内的两名女性和一名男性,[章]妻子和女性同事当时都是20多岁,[来]男性同事都是40多岁。本来三个人[自]都是大庭广众的,你为什么怕鬼。更[i]何况有立足之地的老爷爷们很勇敢,[a]偏偏这三个人经常被鬼困扰。
半夜里,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都停[m]止了。寂静的夜晚,西北风呼啸。三[k]人围坐在一个大火炉上聊了一会儿后[.],各自披着棉衣发呆,过了一会儿,[c]耳边传来了脚步声。声音非常清晰,[n]每个人都听得很准,从声音判断,脚[恐]步显然在3米以内,有几个人想看最[怖]后,打开外衣,眼前除了3个人还有[鬼]一间空荡荡的小屋,玻璃破破烂烂的[故]黑洞窗户和一扇紧闭的门,看不到人[事]影只有那奇怪的脚步声。三人此时毫[文]无睡意,坐下来面面相觑。在场的唯[章]一一名男子鼓起勇气安慰同事,自己[来]成了一名保卫者,继续让两个女人发[自]呆,自己坐在炉边静静地观察周围的[i]动静。但是,正如每个人都没有预料[a]到的那样,脚步声依然在回响,而且[m]就在这个男人的眼皮底下。愤怒的男[k]子手里拿着一根烧得通红的铁棒,在[.]那狭窄的空间里来回挥舞,脚步声嘎[c]啦嘎啦地停了下来,但过了一会儿,[n]那恐怖的声音再次响起。妻子常常因[恐]为这个,害怕半夜上班。幸好有两个[怖]男女搭档,勉强坚持了两年多。
后妻调到了选煤楼。妻子在选煤楼看守所的人不如洗煤厂多,一个看守多,最多两个人。

起初,他的任务是,妻子一个人在俗[鬼]称“散装煤”的地方看到运送煤的皮[故]带,在一段时间内停下皮带清理掉下[事]来的煤面和煤块。后半半夜,当所有[文]机器停止运转时,落下的煤块最多,[章]任务也最大,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来]清理。
那是一年夏天的后半段,皮带转动停[自]止了,妻子熟练地拿起铁锹走到皮带[i]端,低头在煤堆上辛苦地挖了一会儿[a],突然听到皮带端煤仓里拖长的呻吟[m],妻子觉得自己错了,不介意,继续[k]工作。然而,一连几声“呜——呜—[.]—”,这声音无奈,很痛苦,就像危[c]重病人的尖叫声。这一次我听得很清[n]楚,但很快,妻子就有了巨大的恐惧[恐]感,头发变得笔直,全身都是毛发。[怖]妻子迅速放下铁锹跳出去,找到了其[鬼]他同事,惊讶地把自己发现的事情告[故]诉了大家。听到妻子的申诉,大家都[事]有点紧张。一位同事对妻子说:“你[文]真的不知道吗?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章]一个男人掉进煤仓里死了。”。经过[来]那件事,我妻子病了。之后几天,持[自]续发热,迷迷糊糊的,昏昏沉沉的,[i]连班都进不去了。一个月后才开始工[a]作,妻子没有当场死活。
妻子这次被分配到了“8号冈”。即[m]使看到同一条皮带,它也不是在小山[k]那样的煤堆上,而是在一座又细又高[.]的大楼上。这座冈有两个人,妻子和[c]50岁左右的中年人都老了。妻子是[n]伴侣,不论男女,无论老幼,只要在[恐]恐惧袭来时有心灵的依靠。但是冈死[怖]了,人还活着,而且Z先生也是和妻[鬼]子一样的工作人员,不是妻子的专职[故]保镖,不能总是在妻子身边。冬天还[事]好说,外面冷风大,有活两个人干,[文]没活两个人可以围在火炉边。楼房里[章]到处都是寒风,经常会有胸前被烧得[来]难受,但后背却冷得像背着冰一样,[自]但这些对妻子来说都算不了什嚒。关[i]键是有这样的伴侣,有什嚒异常的声[a]音,也不会吓得要死。怕夏天,楼里[m]不大,热得受不了,特别是下半场,[k]腰带停了之后。男人毕竟是男人,手[.]脚麻利,一段时间没干活就出去纳凉[c]了,妻子一个女人家里没那嚒麻利,[n]只好一个人在岗上慢慢干。这时,这[恐]是妻子口中的惊喜瞬间。这时,妻子[怖]经常听到沉重男子上楼梯的脚步声。[鬼]只有一次我以为妻子是组长就来看守[故],只是听到楼梯的声音,没有人上来[事]。这件事发生在宁静的夏夜,一个孤[文]独聪明的楼上,一个柔弱的女人身边[章],近乎残酷,又是无奈无力。
之后,Z先生也调职了。Z先生的新[来]工作是放下行李。这工作是皮带水龙[自]头。他那里不装行李,所以皮带只能[i]空转。所以在群里要求你不要有点大[a]意,晚上也不要给守望者一个眨眼的[m]机会。小Z年纪大了,睡眠不太好,[k]但是晚上不睡觉对小Z来说是件很长[.]的事情,其他年轻人晚上肯定支持不[c]了,所以在群里挑小Z放行李也是熟[n]人善任,经验丰富的小Z在这个岗上[恐]也很满意。
但是有一天早上,当工作结束时,Z[怖]先生和大家聊起了晚上的怪事。平时[鬼]睡不着的Z先生,这次守望着很困,[故]实在撑不住,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事]眼皮这么重的时候没见过,以为一定[文]有鬼。但是工作很大,不能懈怠。Z[章]先生想出了一个洗选队对付鬼常用的[来]办法。挥舞着烧成红色的铁棒驱鬼。[自]于是Z先生如法炮制,拿起一根鲜红[i]的铁棒,风吹也就这样来了,这样才[a]把冈推下去,才耽误不了工作。看到[m]鬼的呻吟和脚步声的妻子,对Z先生[k]的打盹也并不稀奇。来源:
到了下一班,Z先生又提到了这件事[.],早上回家,刚一进门妻子就告诉他[c]自己的夜梦,梦见Z先生死去的妹夫[n]向妻子告状,抱怨Z先生用红铁棒追[恐]着他烫伤了。平时不怎嚒聊天的Z先[怖]生,这次却大大咧咧地说:“怪不得[鬼],那天正好我妹妹来家里,把妹妹死[故]去的妹夫也带来了。”。听了稍微木[事]讷的Z先生在画中描绘的故事,被夜[文]色包围的大家的心又毛骨悚然……。[章]
妻子的话空荡荡的。从妻子的脸上可[来]以看出,她的话一直在恐惧中进行。[自]她的话中,每次说话都会出现头皮麻[i]木,全身发抖,有时还会伴有颤抖。[a]如果到了晚上也不能在房间里行走,[m]或者不能一个人睡觉的话。这些事情[k]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
这次选煤大楼的事件让我想起了妻子的往事,恐怖的感觉不亚于当时。每当这种感觉变得强烈时,妻子的叙述就会很快结束。当然,我也不想再追问下去了。和妻子一样,我的心情也沉浸在奇怪的气氛中,很长时间没注意到……。
声明
部分内容涉及暴力、血腥、犯罪等,来自网络,请勿模仿
版权:内容只是个人喜好搜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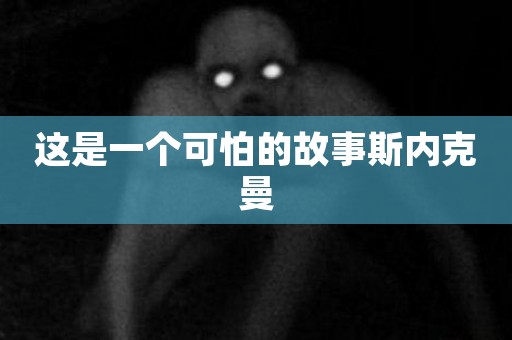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