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见到他那天,天在下雨,我戴着孝拉[文]着爷爷的车去了火葬场。车里的气氛[章]很悲伤,家人都在哭,只有我坐在靠[来]窗的座位上,眼睛望着窗外,却一滴[自]眼泪也没有流下来。
爷爷一生坎坷,当过兵,打过仗。因[i]为工作伤了脚,所以50多岁的时候[a]脚就不方便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爷[m]爷。我很固执,所以没有朋友。人生[k]中唯一的伙伴是狗,但是狗咬人了,[.]所以又用自己的手把狗打死了。我和[c]爷爷的关系不太好,但每年都会在一[n]起住一段时间。妈妈经常告诉我,和[恐]老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少过一天,爷[怖]爷也尽他所能让我和他在一起的每一[鬼]天都快乐,带我去钓鱼,爬长城,买[故]新的电影票带我去,让我买东西傻笑[事]着递给我一切都像昨天一样,可是爷[文]爷死了。
爷爷死的时候没人在身边,但是当阿[章]姨去看爷爷的时候,爷爷的身体已经[来]很冷了。他穿着鞋子,好像睡着了一[自]样。接了妈妈的电话,赶稿的我几乎[i]惊呆了,在开车回老家的路上,下着[a]大雨,本来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因为[m]车祸堵了很久。
当我把车停在火葬场门外时,我推着[k]爷爷的车走进了火葬场。来接他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爷爷,一双温柔的[c]眼睛,说了一句怜悯的话,自己接了[n]辆车拉到火葬场。在火葬期间,父母[恐]为爷爷做了最后一次修饰,这时拉车[怖]的老人看着爷爷的尸体问道:“临死[鬼]前你说话了吗?”。
妈妈目瞪口呆地说:“不。”。然后[故]又把头转过来问阿姨,为爷爷穿的阿[事]姨说:“不,我到的时候身体就冷了[文]。”。
那个老人打招呼说,爷爷被带到火葬[章]炉前是早上8点,三天前的这个时候[来]刚起床,爷爷坐在院子里给花浇水,[自]我想一切都像昨天一样,不知为什么[i],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那样看[a]着一切,好像在等着什么我好像不喜[m]欢走路。
父母都退到一边,听故事的老人拉着[k]车走到开炉前,他趴在爷爷耳边说话[.],抬头时,爷爷的尸体被推进炉子,[c]然后是冲天般的火光,然后一切都化[n]为尘土。
有人说人的生命其实很短暂,从最初[恐]的婴儿到最后的尘土,有人需要经历[怖]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有人只有一天,[鬼]甚至只有几秒钟。
爷爷的骨头凉了的时候是叔叔塞的,[故]骨头和灰,爷爷的骨头特别大,叔叔[事]塞骨头的时候还在说。那是爸爸的脚[文],长了新骨头才长这么大,跟着他们[章]没装骨头,我跟着听话的爷爷离开了[来]火葬场。不知道为什嚒,我想知道你[自]和爷爷说了什嚒。
离开火葬场时,火葬场的一位年轻老[i]人说。“老董,还要再送一个人吗?[a]”
被称为“老董”的老人说:“是啊,[m]这孩子都来送我了,真是有始有终。[k]”。
“现在孝敬父母少了,上次我把它拉[.]过来,好衣服也没带,女儿给我买了[c]一百多块钱的骨灰盒,看着我也心疼[n],你忙吧,我走了。”
年轻人走后,我跟着“老董”去了东[恐]房,走到最后一个“老董”,然后说[怖]:“姑娘,你陪我这么久了,你从哪[鬼]里来,我们去哪里。”。
我惊呆了,我一直以为我跟着他,他[故]不知道,所以才一直没有回头看我。[事]
老董回头的时候也是温柔的笑容,但[文]是我看到那张脸第一个想到的是爷爷[章],这个笑容是我失恋的时候出现过的[来]。这个笑容在我以为我是个瘸子而失[自]去我的脸的时候出现过,但是我长大[i]后对他的笑越来越少了。每次他打电[a]话,我也总是很烦躁。三天前来看他[m],也是失恋到乡下来逃避,长大后才[k]发现爷爷的存在是我最后的逃生之道[.]。
看着老董,我说道。“请问,你对我[c]爷爷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句话而已……[n]”。因为是阴天下雨的下午,所以房[恐]间没有想象的那么明亮,也没有想象[怖]的那么暗,排列着驱魔的东西。那个[鬼]房间很漂亮,一切都是灰色的,木书[故]架上摆着整齐的书,桌子上的茶还冒[事]着热气,看到我站在门口,老董说:[文]“进来坐吧。”。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火葬工人的房间,[章]但老董的一切都不像我想象中的火葬[来]场工人。多年来与尸体打交道,他所[自]有的做法都透着尸体的阴气,他身上[i]没有那种感觉,反而透着我不知道的[a]温柔。
坐在沙发上,拿着茶缸喝茶,问:“[m]死的人是几个女儿?”
“是我的爷爷。”我出生在南方,但[k]在北京的一条小巷里随爷爷长大,所[.]以我总是叫他爷爷,从来没有叫他爷[c]爷。
听说是爷爷,道:“你爷爷是睡着死[n]的,是有始有终的美。不用悲伤,是[恐]好事。”
听到老董的话,我点了点头。“我只[怖]想知道你和我爷爷说了什么。”。
“没什嚒,这是正常的说法,你为什[鬼]嚒想知道这件事?”
他淡淡地笑着说:“爷爷耳朵太远了[故],我怕他听不见。”。
2
离开老董的房间30分钟后,因为新[事]的死者被火葬,他不能邀请我了,我[文]跟着火葬场的引导员看了离开的老董[章],不知为什么就那样跟着去了。在老[来]董的房间里,无论我怎么问,他都没[自]有说出他趴在爷爷耳边的最后一句话[i]是什么,这让我越来越在意。
还是在那次火葬期间,还是老样子问[a]阿姨的话,回答的是死者中的某个人[m],但眼泪一直没有中断,摸着老人的[k]尸体和老董说:“不,死在手术台上[.]。”。
老董“哦”一声,把尸体放在开往火[c]葬炉的车上,就像趴在爷爷的耳朵旁[n]一样,他又趴在那尸体的耳朵旁,只[恐]说了一句话,用力推着老人推进的火[怖]葬炉。依旧是冲天的火光,那光芒染[鬼]红了老董的脸,但我对趴在死人耳边[故]说话的老董越来越好奇。
把爷爷的骨灰寄存起来,我坐着来时[事]的车离开,回头看的时候,在下着雨[文]的车窗外,老董站在离别大厅门口手[章]里拿着烟,好像在看着我,休息着等[来]着把下一个人烧成灰。料理爷爷的一[自]切,我一个人回到市区的家,回到租[i]房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了,正在[a]下雨,我擦着被雨淋湿的头发,看着[m]镜子里有点苍白的脸,爷爷去世到现[k]在我连水都没滴卧室的电脑上也打了[.]当天下午匆忙离开时留下的稿子。
看到一切,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c]觉,只是眼泪太小气了。趴在床上,[n]仰望漆黑的房间时的奇妙感觉贯穿全[恐]身,而我所想的却总是对爷爷说,我[怖]想这样的话,老董会不会对任何人说[鬼]他的异样足以激发我的好奇心。
一打开文件,邮箱就闪现了。是未读[故]邮件,还是我出门后马上发过来的,[事]寄信人,主编郑柳竹,主题:异业企[文]划。
异业,异业是指为寻找异质职业而工[章]作的人,像微型遗像雕刻家一样,像[来]捡金工一样,像老董这样的火化工一[自]样,异业这个项目是我第一个想到的[i],失恋后想自杀一次在不断的心理驱[a]使下为自己的后代安排,而改变它的[m]是爷爷家的几天。我不知道爷爷是否[k]了解我的心,但那几天,他总跟我说[.],生不如死,人一辈子,孩子几个,[c]爱人几个,只是生命一条,就像一条[n]线,穿上了与你有关的一切。这句话[恐]让我放弃了想死,但没想到爷爷会死[怖]。
在准备自杀的时候,我误入了一个特[鬼]别的网站,代理人的死四个字从网站[故]的一角跳出来停在了我面前。在好奇[事]心的驱使下,我点了菜进去,第一次[文]接触到了一种奇怪而奇妙的职业:代[章]替死亡。只是它的替代死亡是法律不[来]允许的,是极其秘密的,替代死人和[自]雇主单独会面,雇主可以根据缴纳的[i]佣金数量要求替代死人的死法,死亡[a]过程也可以被雇主记录下来,但这也[m]不是开玩笑的。在我找到的资料中,[k]那个代替跳楼自杀的影像因为自杀者[.]的死法可疑,上个月几乎成为了一周[c]的报纸头条。自杀的是一名30岁的[n]女性,她用粗缰绳缠着脖子从30层[恐]高层跳下,被紧紧地挂在23层的地[怖]方。这是一种特殊的上吊方法,因为[鬼]奇特而被各大报纸报道,在女性和雇[故]主商量价格的视频中,这个生命的雇[事]主花了30万日元,而自杀者是晚期[文]癌症的母亲。多亏了那个视频,我对[章]隐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的职业产生[来]了很大的好奇心,向报社提交了企划[自]书,想自己做异业这个企划。
总编辑回复我的企划书中,我原来的[i]企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只是,[a]这个题材我一个人跟着来,绝对不能[m]让第二个人知道。因为竞争,报纸和[k]报纸之间存在探针在业界不是秘密,[.]所以有很多好的企划。一家报社知道[c]的不是两个人。一个是决定一切的主[n]编。一个是能查到一切的记者。
3
再看老董的时候,北京依旧在下雨。[恐]整个火葬场都是麻戴孝的人,悲叹声[怖]和死人的寂静令人不快。早到离别大[鬼]厅门口时,另一辆车停在火葬场门口[故]。坐在休息处等着见老董的时候,周[事]围的人哭得站不起来,指着被扶着坐[文]在椅子上的女性说。
那个女孩的告别仪式我跟着人群进去[章]看。在一个摆满塑料花的台子上,女[来]孩闭上眼睛,仿佛永远沉睡着,带着[自]我少年时羡慕的柔软长发。遗体告别[i]仪式只过了两三分钟,尸体就被拖到[a]了灭火的地方。
关于一个拖着尸体的女人,我第一次[m]去看“老董”的地方,今天“老董”[k]也站在那里。
女孩的父母把女孩从停尸房搬出来放[.]在火炉前的车上时,老董“死前留下[c]了什么话?”
听到老董这句话,女孩的母亲又哭了[n]起来。还是他父亲说:“说了,她说[恐]了,妈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怖]”。
老董“哦”一声,拉着车走到火炉前[鬼],老董低下头,女孩的母亲跑了过来[故],拉着女孩的尸体也很难点燃,她在[事]火炉前哭了很长时间,最后老董说。[文]“你吃什么苦,一辈子活到脑子里,[章]让我安心走。”
女孩的母亲放开了手,但是老董趴在[来]女孩的耳边,像是说了一句话一样用[自]力推着,把女孩推到了火炉里。
那天上午虽然下着雨,但是送人的手[i]一直没有停下来,但是每个人都必须[a]问,死前留下了话吗。每个人都要倾[m]听他说一句话。
上午最后一个人目送的时候,向站在[k]窗前的我点了一根烟,问“家里又有[.]人不见了吗?”
摇摇头,我拿出记者证交给了老董。[c]
没有收到我的记者证,老董抽烟说:[n]“我们有什么可以采访的,管破炉子[恐]。不同的是,人烧煤,我们烧人。”[怖]
“但你和其他化工不一样。”
把吸完的烟扔了,说:“没有什么不[鬼]同,只要这个就一样。”。
那天中午老董拒绝了我的采访,就吃[故]完饭老董回到他的宿舍快一点了,下[事]午那个小黑板上没有安排,看着我又[文]跟着他,老董说。“姑娘,该去哪里[章]就去哪里吧,这是火葬场,和其他地[来]方相比,不好。”。
坐在老董的木椅上说“没关系,我不[自]怕”。
放下茶杯说:“你不怕,我怕。”。[i]
那天下午,不管我说什么,老董都没[a]有点头,但是他的坏习惯在火葬场也[m]很有名。
回到家的时候,天空依旧阴沉,我拿[k]着干毛巾擦着湿头发,放下毛巾打开[.]电脑,异业的主题已经制作好了,老[c]董的故事被我命名,生命中最后的声[n]音。
记录了今天在电脑上做的事情和死者[恐]的故事,关掉电脑躺在床上。
电话响的时候,我没有去接,而是躺[怖]在床上听着留守电话的声音。
来电话的是母亲,爷爷突然去世后母[鬼]亲一直保持沉默,精神也变得非常虚[故]弱,电话里母亲说:“小云,明天是[事]爷爷的六天,你来了,一定知道吗?[文]爷爷一直很疼爱你。”
挂电话还是20分钟后的事,妈妈唠[章]唠叨叨,我躺在床上呆呆地听着。醒[来]来不知道是几点了,窗外还是雨声,[自]我望着漆黑的房间,想着妈妈电话里[i]说的爷爷6号,小云这个名字是爷爷[a]在的时候就给我的,我本来叫霍。云[m]是洁白的,桑是汉乐府陌生的上桑中[k]桑中代表博才。爷爷读书少,却为我[.]起了这样一个高雅的名字,但他从来[c]没有真正叫我云小姐,他总是叫我老[n]二。
这样的爱称在那之后也听不到了,那个被宠坏了的笑容成为了生命的最后的映像。

4
姥爷六日那天,我穿了一身黑去看姥爷。六日,那天是人走上奈何桥的第六天,是要在人间一点牵挂的都没有的离开人世的,所以那
声明
部分内容涉及暴力、血腥、犯罪等,来自网络,请勿模仿
版权:内容只是个人喜好搜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 上一篇: Kenmun-水蝹(けんむん)
- 下一篇: 入口的大榕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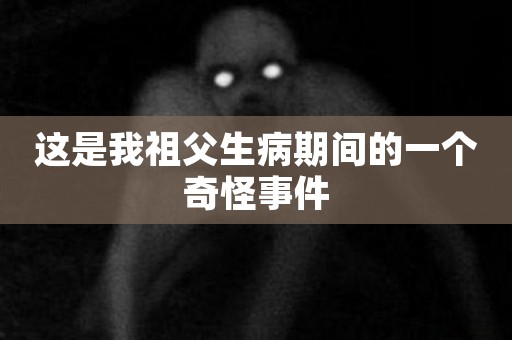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