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各位,最近一个月比较忙,所以没什幺消息。但我很高兴告诉你们,在昨天晚上我终于抵达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我现在在我人生中住的第一间美国饭店的旅馆发文,房间外的风景宜人,可以观赏到州立医院和当地监狱,真是段美好时光。
如果你和我在同个城市,或者你有任何资讯,就留下讯息吧。
─────────
左右游戏〈手稿1〉15/02/2017
随着黑暗逼近,我在自己的潜意识里被拽向更深更深的底部,直到我沉降在脑海深处,到达一个无法言喻的地方。这里毫无特徵、不存在任何方向也没有时间概念,这片虚无存在于人生最虚弱的时点。
我感觉自己正向远方漂流,屈服于一道难以察觉的浪涌,缓慢却无情地被带离世界。
夜晚剩下的记忆片段像是稍纵即逝的快照。
我隐约地感受到躯体被抬离地面,在我移动穿越森林时,四肢被重力下拉。
不知过了多久后,我感受到身体右侧明显的灼热感。在我现在身处的世界中,只能接受痛楚的传来的回音,但我知道疼痛已经产生过。我无法再参透更深的涵义,于是放任感官消逝,随后再次地沉入静谧的黑暗中。
当我的双眼终于睁开时,太阳正开始升起。身体完全使不上力,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透过睫毛,望向面前模糊的景象。
我位于Wrangler的后方,倚靠着行李的软柱。有个人在我身旁跪坐并揪着我的右边肩膀,当我试着叫唤此人时,我发现我的声音虚弱到只剩丝丝细语,如此孱弱以致几乎听不见。
AS:…罗柏…
听见我的声音后,人影转向我并跪在我面前,凝视我缓慢恢复对焦的双眼。
罗柏:请放鬆躺好夏尔玛小姐,我刚将妳包扎好,但我还须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AS:你…你后来怎幺了?
罗柏:丹妮丝开枪击中我之后,我假装已经死了。当她进入森林后,我便能自由行动,我带着急救包进入树林里,将自己稍微包扎。当我听到那可怕的声响后就赶来帮忙,在察看的时候就发现了妳。
AS:…车子引擎正在发动?
罗柏:我想先帮妳温暖车内。妳已经受到惊吓,再说车子电池也不会再消耗,所以我就─
AS:不我是指…怎幺启动引擎?那把钥匙,它已经─
罗柏:妳以为我会只带了一把钥匙,冒着风险走这幺远?
罗柏看起来觉得受到污辱似的,回想旅途中我对他认知的一切,我可以了解为何他会有这种感觉。儘管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虽然想当然地只能发出稀微的喘息声,轻声地飘散于空气中。
AS:我想你不会的…这实在非常像你的风格。我想昨晚蓝鹊应该非常想要这个得到资讯。
罗柏:对啊,但,她没问。
AS:…我很高兴你撑过了罗柏。
罗柏:我也很高兴你撑过了。伦敦来的人就是坚强。
AS:我是从布里斯托来的。
罗柏:当然…对,那是当然…抱歉…
罗柏试图恢复笑容,但笑容很快地消逝。随着笑容不再,他面容突然变得畏缩,露出无法控制的哀伤。
罗柏:夏尔玛小姐,我很抱歉!非常抱歉!
罗柏古萨德饱受风霜的脸顿时布满泪水,他朝向我并不断说着抱歉两字,他的双臂环绕我的腰际,将头靠在我的左肩上。我将如铅一般重的手抬起,抚过他的头髮,将他靠向我。
当罗柏持续哭泣时,我缓缓转头看向右方,查看我手臂的伤势。昨夜里,混乱的疼痛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势,大量失血和刺耳的声响,让我无法顾及受伤的细节,原始本能驱使我忽略伤势继续前进。现在情形不同了,我沉浸在罗柏宁静的温暖中,能够充分的评估我受伤的程度。
我失去了右手手肘以下的部分。
这像是梦境一般,我的上手臂依然保持完整,除了一些昨夜跌落时造成的瘀青,再向下仅仅一段距离,手臂骤然停止,连接着的是超现实似的断肢末端。伤口本身被遮住,以洁白的绷带包扎起来。
我无法确定我应该要有什幺感觉,因此,我像是感觉不到任何事物一样。
AS:没关係罗柏,没关係。
罗柏:我从来…从来不希望事情变成这─
AS:我理解…我理解。
罗柏身体向后倾,眼中仍泛着泪水。
罗柏:我会带妳回家,好吗?我会找到可以回头的路,我们会带妳回家的。
我可以感受到罗柏的提议是真诚的,老实说我有一些惊讶。我仍记得在隧道口我们曾口头约定;不到这条路的尽头,他绝不会回头。我没想到,他会是违背这个约定的人。
我理解这是将这一切置于身后的最佳机会,从这条恐怖的道路逃脱,在它进一步蚕食我之前。我知道回头的路,它通向安全、通向家庭,通向正常的生活。然而我脑中传来隐晦的声音,悄悄地诉说着,这幺做将不会得到一切的解答。
AS:…如果你想继续的话,我仍在游戏中。
罗柏露出了伤心的微笑,如果还有力气的话我会回覆他。那一刻,我们之间沉默却互相理解对方,这是一种默契,在看过并经历这些事情后,我们仍选择追寻这条路的奥秘。这个决定揭示了一部分的我们,披露出我们行为背后的那股动力,不顾生命安全,甚至遮蔽了挚爱的人的无声抗议。
这是只有两个支离破碎的人才会做的决定。
罗柏花了早上的时间整理Wrangler,让我有时间休息。令人惊讶的是他四处走动,以他一贯的步调做着例行公事。我逐渐感受到生命力重新在血管内流动,我不禁思考是否那神奇的力量支持着我们两人,包括Wrangler的燃料箱,都得到了温和的恢复能力。这个概念理应让我感到慰藉,但取而代之的是,我却觉得像是置身水族箱的龙虾一般。
几个小时后,罗柏将我移动到车外,让我倚靠着门框。在我面前有三个土堆,从地面上微微隆起,其中两个上方有着十字架,十字架是用几根树枝牢固地绑在一起而成。最左方的坟上光秃一片,代表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AS:那是…蓝鹊的?没有十字架?
罗柏:我想她并不需要。
AS:你知道她不会像你一样这幺做的。
罗柏:那好消息是我并不是她。我尽我所能的埋葬她,但她的身心状态就是那样,是那孩子杀死她的吗?
罗柏将折叠铲丢进车子的后方。过了片刻,我选择不回应他对蓝鹊的陈述。
AS:不,它没有…是我杀的。
罗柏突然转身走回来,眉头困惑紧锁。
AS:我将C4炸药装进我的背包,当她拿走背包时,我…嗯…
我示意那座光秃的坟墓。罗柏像是第一次见到我般地看着我。
罗柏:妳是从哪里─
AS:从你儿子的车里。
我注意着我平静的言语传到罗伯的耳里,这句话的涵义钻进他的意识里,话中的意义使他的面容扭曲,呈现被羞辱且带有点被揭发的愤怒。
我能透过他的反应得知我是正确的。
从我得知他儿子的名字后,我们还没有机会讨论这件事。这个讯息构成关键的线索,将路上遭遇到奇怪且看似不一致的事件连接起来。在这星期的早些时间,我有点担心必须面对罗柏,与他谈论这个讯息,但现在情况不同。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我们已经经历太多,如果他真的想要将我带我到某个具有恶意的地方,我也毫无方法且无力去阻止他。
AS:我想是时候开始我们的第二段访谈了。
随着紧张和有些罪恶感的沉默,罗柏点了点头,帮助我进入车内乘客的座位。
───────
罗柏:那不是军用的,是商业用途。
Wrangler继续穿越森林。我持续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沉默,让罗柏以自己的言语,照他自己的步调回应。
AS:商业用途?
罗柏:对,炸药是用来拆除建筑的。那是巴比的工作,他拥有自己的公司。
AS:你一定引以为傲吧。
罗柏:对啊…对,他从白手起家到建立起公司。造访他的办公室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AS:所以…他最后是怎幺来这的?
罗柏安静下来,勉强接受他必须从头开始说起。
罗柏:…巴比是聪明的孩子…比我以前还聪明。15岁时他可以接手农场,但他不喜欢乡村生活。反而搬到凤凰城,取得大学的学历后,开始稳定的职涯生活。
AS:稳定的职涯生活?对古萨德来说算是非常叛逆啊。
罗柏:哈…嗯我们算是相当不同的人…并不是永远都能相处得来。我当时还是一名信差,随时搭机前往新的地方。想当然尔我也造访过日本,在那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
AS:青木原(Aokigahara)。
罗柏:没错,那改变了一切。五年后我回到家,有了新的嗜好。巴比并不在乎那些故事,但…他妈在我离家时突然过世。我们都想要重新来过,更多参与彼此的生命,所以…他和我一起到太平洋的西北边,找寻大脚野人的蹤迹。但那生物始终不见蹤影,不久之后他自己进行研究,组织旅程,蒐集遍布全国各式关于怪奇事物的流言。
AS:听起来那是一段属于你们的美好时光。
罗柏:的确是。
AS:所以…是巴比发现左右游戏的吗?
罗柏:…某天他突如其来地打电话给我。大约是三年前,说他发现了一套规则,说我们应该要试试看。老实讲,我那时觉得我们的旅行生活已经终止了。我回到阿拉巴马州,而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但他突然要我到凤凰城和他碰面,我理所当然地前往赴约。
AS:而这一次,你们都意识到这次是玩真的。
罗柏:巴比在抵达隧道时就立刻知道了,他每天从那裏经过,知道那裏不应该会有隧道,但…隧道确实出现在那。他说这是他所见过最惊奇的事,隔年我们只要一有时间在一起,就会绘製这裏的地图,但我们相当缓慢地行进,慢慢勾勒出这地方的样貌,我们规律地回头。花了一阵子的时间才有勇气在路上过夜,我们俩都害怕隧道会消失或什幺的。
我能看出罗柏在脑中回忆这些事件,这些回忆几乎让他笑了出来。
罗柏:巴比的妻子就像是洋娃娃一般,在他的办公室工作,是我见过最亲切也最有趣的女孩。他们年龄相差十岁,但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多幺相配。他与她分享所有事情,包括这条道路,在巴比熟悉规则并觉得安全后,他们开始一起描绘地图…探索属于他们的小世界。
在稍作停顿后,罗柏的表情些微低沉,回忆逐渐变得黑暗。
罗柏:几个月过去,巴比越来越少与我联繫,这是我预期中的事。接着有天夜里,我接到一通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我的孩子在凤凰城的急救室里。
AS:他还好吗?
罗柏:不,他情形不太好,腿部严重损伤,神智不清,呼喊着玛乔丽的名字。他们在他的车内找到玛乔丽的背包,但…她却不见蹤影。
AS:巴比在那条路上失去了她。
罗柏:对,没错。
AS:我们来这的第二天晚上,在我们失去王牌后,你说过这条路以前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罗柏:嗯,我至少没有说谎。并不是这条路伤害他们的。
AS:…那是什幺意思?
罗柏:他们到达森林,以前没有人走到那幺远,但…这次他们比以往走得更远一些。
AS:你知道原因吗?
罗柏:他们即将要有一个孩子了,玛乔丽接近临盆…旅途将变得很不容易。我想他们知道他们会有一阵子无法踏上这条路。这就像是嗯…最后一搏吧我猜。
AS:但只有巴比回来?
罗柏:他们探索树林直到夜幕降临,当巴比说他们必须回头时…玛乔丽不想这幺做。他从未跟我说原因,从未跟我说发生了什幺。那趟旅行结束后,玛乔丽仍待在那,而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罗柏花了片刻整理自己的思绪,将各个事件依序排列。树木开始变得稀疏,阳光透过车棚宽大的空隙洒落,看起来我们正接近森林的尽头。
罗柏:巴比花了一个月多的时间复元,那孩子死命地想要把妻子找回来,而他当然的也成为造成妻子失蹤的嫌疑犯。不用多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启程踏上道路寻找玛乔丽。
AS:但他没能找到。
罗柏:不…他找到她了。只是,嗯…比他预期的还要快一些。
我花了片刻解读罗柏话中的含意,突然我感觉一颗石头重重的砸落在我的胃中。
AS:她出现在第34个转角。
罗柏肃然的点了点头。
罗柏:当然她不再是巴比所认识的那个女人。整天站在那儿,喃喃自语说着关于路的事,甚至根本不认得他。我记得巴比第一次在那见到她时曾经打给我,他心都碎了。从那天起他试着每天停在那个转角,他试过叫喊,试过恳求,试过给她带上照片和礼物,但…她从来没有回应过。不知道那人是否真的是玛格丽,但不论位于那个转角的是什幺,都已经是属于这条路的了。
罗柏:巴比在那个转角失去了什幺。一阵子后,对这个游戏的着迷,逐渐变为酸楚,变为憎恶,他认为这条路是某种邪恶的事物,无法与我们的世界连接。
罗柏:那时我常相隔几天就打电话关心他。某个周末,他说他感觉好些了,甚至说他重新开始工作。我想或许事情有些好转,但…接着他变得沉寂,三天没有接电话。当时我在凤凰城有个住处,也有一份他房子的备份钥匙,就是在那裏发现纸条的,上面写着他已经再次踏上路途,最后一次尝试去找他妻子…如果他没办法将她带回来─
AS:他就会摧毁那个隧道。
罗柏:将路与世界切割。我在凤凰城、芝加哥和一些不同地方玩过这个游戏,但就是那个隧道能让你通往道路。我四处查看他的车库,找到电话的盒子,大量子电子零件散落各处…他做了甚幺已经满明显了,所以我跳上我的车子。
我们开车通过森林,走在一条狭长的路上。在远方,可以看到道路通向高耸的砂岩,更后方是连绵的山脉。
罗柏:在我抵达欢乐镇前,他在回程途中开车经过我,全速在路上狂飙,发疯似地开着车,那时我就知道他并没有找到她…他打算要摧毁隧道,将这个游戏彻底中止。
AS:但他始终没有走那幺远。
罗柏:我试着跟他联络,打他的手机,试着用无线电呼叫,他SIM卡的资料上有一组电话号码,我的老天我甚至传简讯到那个号码。最后,我和他竞速驶回凤凰城,他开得比我快,但我的技术比较好,在我经过几个难过弯的转角后…
AS:你将他逼离道路。
罗柏望向远方的山脊,他的双手握着方向盘。
罗柏:手机过了通道之后没有讯号,这点他知道。他要不在这一侧引爆炸药…或者他在隧道时引爆。
AS:所以你是试着救他或救你自己?
罗柏:都不是。我试着救这条路…随妳怎幺看待这个地方夏尔玛女士,但这里是一条摆脱所有已知事物的门廊,一条摆脱…摆脱现实的道路。它可能是我们曾穿越过最特别的疆界…一部分的我认为,它是如此地重要,不能让人将它破坏。
今天第二次,罗柏泪流满面,也是第二次,他如此受挫。当他继续开口时,眼泪无声地滑落他的脸颊。
罗柏:他比我想像得伤得更重,在他遇到我之前就已经受了重伤,这也是他想要快点到达隧道的原因,他想要趁他还能完成时摧毁它。
罗柏:这条路几乎夺走他的所有,而我将他所剩下的夺去…我浇熄他的希望,夺去他的机会,不让他以自己的方式离开这世界。到最后他甚至看起来并不愤怒…他只是问起玛乔丽,问我为什幺她要这幺做,为什幺她要离开。我让他留在那裏,我常常重回那个地方,但…我始终没有很好的答案,就是那时候,我开始準备下一趟旅程。
AS:所以你把他的日誌上传到网路上,假装是你发现的。
罗柏:我认为这幺做的话,人们会比较不会起疑。
AS:那幺为什幺我们全都被扯进来?为什幺你要带我们和你来这里?
罗柏:我猜…我想是因为我认为是时候让世界知道了。不想让这里最后沦为一个老男人秘密,我对天发誓,如果早知道这条路会…我绝对不会带你们来这里。
罗柏的面容变得紧绷,露出羞耻和充满罪恶感的表情。我不能说他并非罪有应得,儘管显露出他的意图,吐露出他的忏悔,这个男人还是驱使自己克服危险,解决逼近自己的难题。这条路上隐藏的秘密已经害死了许多人,他仍隐藏自己最重大的一个秘密。
嗯,或许并不是最重大的。
AS:其实并不是你将我俩带到这里的,罗柏。
罗柏转向我,充满疑惑。
AS:昨晚我在树林里遇到了一个人,一个人形,就像你在日本看到的那个一样。「看起来就像电视萤幕上出现的杂讯」…我想那就是你,罗柏,我想我见到你了…在多年以前…
以我目前的身心状态,还有这些事件产生的机制,背后令人震惊的谕示,已经远超过我能以言语解释清楚的範畴。于是,我仅仅举起我残余的右手臂,静待罗柏发现其中的连结。
片刻后,车子发出刺耳声急煞停止下来。
罗柏双目直视前方,在方向盘上的指关节转为苍白。我清楚知道在他石化似的面容底下,每一寸的大脑皮质正在努力理解这个新的启示。如果这是真的,在那片静谧的森林,我不知怎地遇见了几十年前年轻的罗柏古萨德,这改变了所有事情。
交错的时间轴带领我们汇集在这个时点,罗柏对怪奇事物产生的癡迷,他儿子悲剧的命运,都起源于那一个单一的时刻。在我出生十年多以前,我已经将我们两人领到这条路上,这条路将我导向他的家门。
如同这条路频繁显露出的混乱,那个在森林里的时刻,揭示了某些更深层的、别有意图的事物。
罗柏暂时踏出车外,随后无言地进入车内,点燃引擎。随后我们又陷入沉默,迷失在脑海里,继续开向砂岩山脉中。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穿越窄小的山路,像是被吞噬似地通过一道扭曲的岩壁。当我们穿越到达另一边时,岩壁上推叠的石块崩落下来,我们之下的地貌完全改变,映入眼帘的是奇特且令人屏息的风景。
Wrangler正在横越悬崖,悬崖之下是广袤平坦的沙地,一片阳橙色的荒原,延伸至所有目光所及的地方。我只能勉强辨识出一条路,切割出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通过我们下方的沙地。在这一片毫无特色的开阔地上,一群独立式结构的玻璃和金属材质的柱体从地上耸立,一条条网状相互垂直的街道将它们连接起来。
AS:那是座城市…路上有座城市。
罗柏保持双眼直视,儘管我们下方有着史诗般的壮阔城市风貌,我仍能可以看出他的神智还在别处,他还在消化我们之间访谈的内容,随后我想最好还是任他独自思考。
我们在山脉中又开了二十分钟,才抵达沙地的平面。我们面前的景象分成两种样貌,藏红色的沙地和湛蓝色的天空,由一道细长平坦的地平线切开。唯一横越这条完美分界的物体,是城市巨大粗拙的灰塔,拔地而起高耸入云。
我们沿着沙地上的路,像蛇一般前行,越向城市边缘试探靠近,城市就越显得越巨大。在我们穿越城市与沙地的交界时,产生一股奇异的对比,当沙地映射出的红铜色转变为灰色时,炎热的气温瞬间凉爽起来,而最明显的是,这里完全连一点细微的声响也没有。当我们探索一条空蕩、维持良好的街道时,我发现我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车子稳定的引擎隆隆声。
AS:这里静悄悄的。
罗柏:这我还能接受。
AS:你觉得是谁建造这个地方?
罗柏:不知道,或许是将我们带来的事物,又或者根本没有人建造…它就是存在。
我思考它是否是对的,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地方会因为任何实际的目的而存在。这城市不知为何看起来就不对劲,就好像是从臆想中捏造出来的,创造它的建筑师只有透过模糊的谣言来了解城市的样貌。这城市具有各种景色,摩天大楼、街灯和擦窗平台,但不具有更深层的事物,就只是个空壳,沙漠中的一个装饰物。
在我们转弯经过接下来几条路时,我望向这些独立式建筑,每一栋至少都有一百层楼高,我的目光由上而下扫过无数个黑暗的窗户,心里想着住在这种地方会是怎样的生活。
当我望向地面那层,答案揭晓了。
那裏有个年轻男子就站在一楼的窗户旁,他的手靠在玻璃上,身穿深灰色西装,表情几乎像是中邪了,他的嘴张开,双手颤抖,眼睛不眨一下直勾勾盯着我们开车经过。
我的目光迅速重回到摩天大楼的玻璃面上,仔细第一排一排审视每一列的窗户。我天真地以为这些建筑是无人居住的,这个地方就只是个巨大的幽灵城市。现在我理解到并不是这样,每一块玻璃都像一潭黑水,表面平静无波,潭底却隐藏极深的恶意。
几秒钟之后,更多人出现了。起初并没有很多,只有几个零散的人影站到窗前,将自己贴进玻璃窗。然而就像濛濛细雨突然爆发成倾盆大雨一般,他们出现的速度翻倍,接着变为三倍,直到没有一扇玻璃是空着的。
车子好像缩小了,受到无数的目光审视,在每一层楼,每一扇窗户,他们全部身穿单色正式服装,向下盯着我们,就像是群盛大法庭上的使者一样。当车子通过时,他们眼神虽然保持直视前方,但很明显地有查觉到我们的存在。
AS:罗柏。罗柏,那裏有─
罗柏:我看到他们了。
罗柏将脚踏向油门并驶离那栋建筑,摆脱上千双目光的重量。当我们通过最后一扇窗时,我向后瞥了一眼,希望看见他们回到建筑深处。但在那最后几个瞬间,我目睹了他们从整齐划一转变成集体陷入绝望的疯狂,口中发出无声地尖叫,拳头重重地敲着玻璃窗。
回过头来,我望向车子经过的侧边建筑,里头的人形都已经站到窗户前,状态已不复冷静。
AS:罗柏,我们要开快点。
罗柏:我这就加速。
随着罗柏重踩油门,Wrangler再次发出兇猛的低吼。我们準备绕进下一个转角,罗柏一边扫视着任何隐密的岔路,一边加速行驶,我痛苦的在座位上转身,注意着我们身后的景色。
窗户的玻璃碎片开始如雨般掉落至柏油路上,看着碎玻璃在空中翻滚,很明显的,这座城市会这幺安静并不是因为没有任何活动,倾泻而下的碎玻璃完全无声,就连摔落在不透的地面也亦然如此。
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东西都发不出声音,除了我们以外。
车子打雷般的引擎声从没这幺巨大过。
向上望去,看见上百双手抓住碎玻璃的窗框,我无法移开视线,上千双油亮的黑色皮鞋跨越窗格。人形从每一层楼涌出,形成一股超现实的人类洪流。
第一波坠落地面,随之而来的是更多人落在他们之上,一堆人形正竭力地挣脱其他人。就像欢乐镇的居民,和其他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人一样,他们不会受到致命行为应该带来的伤害。那些以双脚落地的人,停止后转而朝向我们,开始追着车子疾跑。剩下的仍在扭动的人群没花多久时间就挣脱了,他们疯狂地踩踏,狂乱地奔跑,发出无声地尖嚎。
就算在他们疯狂的追赶之中,当玻璃像不祥的恶兆从每一栋经过的建筑倾泻而下时,这世界仍然保持寂静。混乱在这片妖异的宁静之中变得更加捉摸不定。
罗柏开往下一个转角,车子甩尾开上一条开阔的长街。眼前这条路摩天大楼夹道耸立,一路延伸至远方渺小的消失点。当我们抵达下一条路宽阔的交叉路口时,不断增长的暴动人群狂冲到我们后面的街道,将整个转角佔据并持续朝我们的方向前进。
一瞬间后,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钻入我的脑袋,这不像我以前有过的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概念,比较像是混合直觉和既视感的一种预知,就像对我来讲非常明显必须要做的事,儘管我并不知道原因。
我发出比细语更大的说话声。
AS:罗柏,我们必须将某个东西丢在我们后方…某个发出巨大声响的东西。
罗柏:妳有什幺打算?
AS:我…你必须相信我,好吗?我们还剩下大部分的塑性炸药,你可以─
罗柏:不,如果你已经把雷管用掉了,我没有时间再做一个新的了。
罗柏瞥了一眼后视镜,随后视线重回路上。我几乎能够听见他脑袋中齿轮转动的声响。
罗柏:但那是我们唯一的炸药,你觉得妳可以开车吗?
AS:试试看吧。
车子迅速驶过路面,我笨拙地握住方面盘,将我的脚移动到油门上,罗柏抬起身子爬向车子的后方。在我虚弱的状态下,每一个颠簸都会让我的骨头嘎吱作响,随着每次换档,我被迫要用剩下完好的那只手臂,横越过去操作排档桿,动作非常不稳定和彆扭,我疼痛的四肢向魁儡般被意志力和肾上腺素驱动,维持稳定的每一秒钟都像是一场搏斗。
前面上方的窗户正开始碎裂,车子持续发出声响,整个城市準备抵制我们的到来。在身后,我可以听到撕胶带的声音,还有撕裂布料和行李落下的声响。我不确定在后面发生了什幺事,我必须相信罗柏的计策。
在到达十字路口之前,我听见后门打开的声音,接着是金属刮擦车底的声音,随后罗柏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将某个东西丢到我们后方的路上。
接近路口时,我将手沿着方向盘摆动,使它向右快速旋转。车子过弯进入下一条路,我的心剧烈下沉,我们被超越了。前方的窗户已经碎裂,前门已经毁坏倒落在街上,建筑内丧心病狂的居民朝我们暴冲,阻挡我们唯一逃脱的路径。
我用脚重重的踩在剎车上,车子倏地停止,引擎停止发动。街道现在已经满溢,压倒性的人群从四方往我们的位置汇集。我回头看向罗柏,他触及我的目光时,颓丧的双眼映出终结。
一股爆炸颤动我们身后的空气,我看向后方的窗户,一个碎裂的汽油桶,罗柏现在已经不需要它来储存油料,它深绿色的外壳已经严重被破坏,内容物喷溅并洒落在道路上。引擎现在没有在转动,午后的空气中,迴荡着爆炸的声响,和原始平静的火焰发出的吼声。
疯狂的人群行径瞬间改变,他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安静的车子上,在前方的人继续奔跑穿越我们,经过车子后争先跑向溢出的汽油,双手插入火焰之中,绝望地抓取熊熊烈火。
小心翼翼地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我爬出驾驶座,和罗柏一起待在车子后座。
他疑惑地对我低语。
罗柏:为什幺他们不注意我们了?他们怎幺了?
AS:…因为声音,他们想得到声音。
我不知道会什幺我这幺确定,但我知道就是这样。城市的居民疯狂地找寻每一个断裂的碎片,将汽油桶撕裂得越来越小,发出嘎吱声和尖啸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火焰逐渐消减,人群变得越发苦恼,就好像珍贵的物品从他们指缝中滑落一般。
AS:他们并不懂。他们将碎片撕扯开,试着找寻答案却徒劳无功…然后他们就会再度安静下来。
罗柏:妳怎幺知道这些的?
AS:我不知道,只是,嗯…只是一种感觉。
罗柏:嗯…我确定他们原本会把我们撕裂,我觉得我们还算满幸运的。
AS:哈,对阿…满幸运的。
当最后一点汽油被燃烧殆尽,火焰熄灭,城市居民停留在街上。他们的奖赏消逝于虚空之中,缺乏立即性的目标,人群的绝望淡化成沉默的沮丧。我看着他们经过,无数的脸庞饱受悲伤的折磨,漫无目的地移动形成一片孤独的海,这片灰色海洋漫过荒凉的城市。
车子现在漂浮在这片海中。很明显如果尝试打开引擎,会使整个城市转而针对我们,燃起他们徒劳的希望,使他们撕毁我们的车,和车内的一切。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完全陷入困境。
罗柏:别担心这些,好吗?
AS:我不觉得他们将会离开,罗伯。
罗柏:他们会离开的。
AS:好…那是何时?他们仍将四散在各处。
罗柏:嘿,我们是一对机智的搭档,我们会想出方法的。
怪异的冷静包围着我们,我在罗柏身旁向后坐,靠着背后的座椅,没有任何事情能做,只能等待情况有所改变。在看了外面的人形超过一个小时后,我唯一感到不同的,只有奇怪的针刺感从已不复在的前肢传来。
AS:我的哦…我的手臂好痛…这怎幺可能─
罗柏:别担心那是,嗯…称作幻肢的症状,妳仍然有感觉对不对?就像那裏还存在着手臂?很多人会有在截肢之后会有这种情形。来…
罗柏手伸到急救包,拿出了蓝色瓶子的药罐,将瓶盖扭下,将两颗药丸摇出来。
罗柏:妳会需要他们来止痛。
我看了一下药罐,随后从他摊开的掌心拿走那两颗药丸。他递给我他的水壶,我喝了两口少量的水将药丸一起服下。
AS:你有很多处理断肢的经验?
罗柏:…比你想像得还要多。
我皱起眉头,虽然我的问题只是随口问起他过去的经验,罗柏的回答却异常真挚,片刻后我才理解其中的原因。
AS:我忘了…你也曾经被徵招入伍。你从没谈过这件事。
罗柏:我还是常常回忆,一群陌生人因为空虚的假设而聚集在一起,被一个老骗子告知,我们这幺做是为了远大的目标。很有趣吧,时间循环一般地又流了回来,我想起来了,他也是开一台吉普车。
AS:罗柏…我跟你说过了,不是你带我们到这里的─
罗柏:那不能改变什幺,不能改变我所做过的事….对妳,对巴比,对任何其他的人。或许妳真的在那森林里,但我是先开始的人,那个一直追问到底路的尽头是什幺的人。
AS:那你觉得是什幺呢?罗柏。
罗柏:我开始觉得我不会知道答案,长久以来我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看过其他人们定居下来。就我所见,决定在哪里停止,路的尽头就在那裏。
我将头靠向罗伯的肩膀,他温柔地用手臂环绕我。没过多久药效开始发作,悄悄地接管我已经虚弱无比的身体,痛觉开始消退,我的其他感官也跟着麻木。阳光仍然透过挡风玻璃照射进来,我的双眼开始慢慢阖上。
我看着人形经过车窗,我的眼皮越来越重。
AS:我不想这样就结束,罗柏。
罗柏:我懂夏尔玛小姐,我懂。
在我陷入无梦的人造睡眠以前,我最后一眼看到的,是罗柏古萨德将手伸向那把步枪。
当我睁开双眼时,太阳已经开始下山。
我被移动了,随着我的视力逐渐回复,周遭开始变得清晰,我仍然在车子里。我的头枕在一堆乾净的衣服上,一条柔软的旅行毯盖在我的身上。
我环顾四周发现罗柏不在。
我一瞬间忘记车外的状况,想要尝试呼叫罗柏,他的名字梗在喉头,因为我看见蹒跚的人形走过车窗,绝望地紧握双手,长长的人影映在车子上。
我重新提高警觉,把毯子掀开放到另一边,缓慢地移动向前。
驾驶舱里同样是空的,除了从我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条,它躺在驾驶座上,小小的且被摺叠起来。当我打开它时,我发现了我的耳机,纸上写着整齐地写着八个字:
「频道一呼叫所有人。」
我将纸条仪表板上,双手开始发抖,慢慢爬行穿越,平缓地移动到驾驶座。我的心脏快从喉咙里蹦出来,我把手机插入CB收音机的插孔,颤抖地吸了一口气,按下第一颗按钮。
AS:罗柏?
罗柏:我嗯…我很抱歉夏尔玛女士。
AS:罗柏,你在哪里?
罗柏:在这条路离妳不远的地方,我爬到其中一个屋顶上。我知道我会永远讨厌这座城市,但是一旦爬上来这里,这风景真不是盖的。
AS:回来罗柏,回来…拜託你。
罗柏:我希望可以,如果能真的这幺做的话。但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东西不会离开的,妳也需要开车前往妳将要去的方向,所以…我能做最好的事情就是製造一些骚动,将他们从妳路径上引开。
我将头靠在方向盘,抱住自己以承受他话语中的重量。
AS:没有你我做不到。
罗柏:那不是真的,夏尔玛小姐。我想无论这条路上有什幺…它希望妳能走完全程。我所想做的就是带妳到这幺远的地方,现在妳不用管我了,妳可以转头踏上归途…但不论妳作何选择,只有我们之中的一人能够离开这里。所以我想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妳想往哪边走?
AS:嗯…你在我前面还是后面?
罗柏: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这是妳的选择,夏尔玛小姐。
在罗柏的话语背后,在抉择的阴影之下,我沉默了,并不是因为这个选择很困难,而是因为我很惭愧地觉得这很容易,在我第一次进入这部车子时就已经决定了,此后每个複杂的时刻都更加深这个决定。我的人生已与这股渴望相连,渴望去理解、去领会、去发现真相,但我从不知道这股渴望已如此深植内心,当其他人事物被剥夺时,我却还是能殷切地忍受。
我直视着后视镜,第一次看到自己,我必须承认我很害怕。
AS:待在你现在的地方,罗柏。
罗柏:哈…好的夏尔玛小姐…妳準备好了吗?
AS:…是的,我準备好了。
罗柏:好了那幺…该是这东西发挥用处的时候了。
枪响从收音机里传来,随后微弱的回声从城市宁静的空气中传来。
城市居民立刻就起了反应,集体忧郁的模样立即消散,转变为新的面容。在我理解以前,分散的人形重新联合起来形成乱窜的人群,奔跑经过车窗,跑往路的后方,朝着噪音的源头前进。
罗柏:他们开始移动了吗?
最后一个居民从我身后消失,我将手越过方向盘,下移到发动开关。
AS:对…对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罗柏:好,那…妳还在等什幺?
随着钥匙决定性地一扭,车子发出怒吼重获新生,轮胎摩擦柏油路面,带我穿越城市的街道。当我离开十字路口时,我看到一小队追赶的人冲过我身后的转角。
罗柏再次射击步枪,持续引起大部分居民的注意。剩余散落的人在我的后视镜中渐远,无法再追上车子。
我先左弯,接着在下一个可以右弯的地方向右转弯,然后再一次左弯,几分钟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开在最后一段路上,带领我回到开阔空旷的沙漠中。
罗柏:所以,妳会做到吗?
AS:是的,我将会做到的。
罗柏:很好,那非常好,夏尔玛小姐,如果,嗯…如果妳找到玛乔丽,如果妳有机会能让我知道…嗯我并不值得知道但─
AS:当然…当然我会的。
罗柏:非常谢谢妳,好了,他们就快到我这里了,所以…我暂时不会跟妳对话,如果我呼叫妳,妳就知道我成功逃脱了,如果我没呼叫妳…妳就当作我已经逃脱了,好吗?
AS:拜託你告诉我说你将会没事的,罗柏。
罗柏:…跟妳一起驾驶是我真正的荣幸,夏尔玛小姐。
最后一声枪响透过收音机迴荡在空中,回音很快被怒吼的引擎声淹没。我冲出城市回到沙漠路上,世界在我身边改变。
前方的路途充满庞大的可能性,然而在我穿越这片广袤的沙漠时,我想起的只有我在身后留下的事物。罗柏J古萨德有他的缺点,他失去过,也曾被癡迷驱使,他的好意往往为悲剧和心碎铺路。
当眼泪从我的双颊滑落,我决定以不同的方式记得他,一个珍视的朋友,一位正直的男人,其余的一切,则是一段伟大的故事。
无论这个故事是如何被人们传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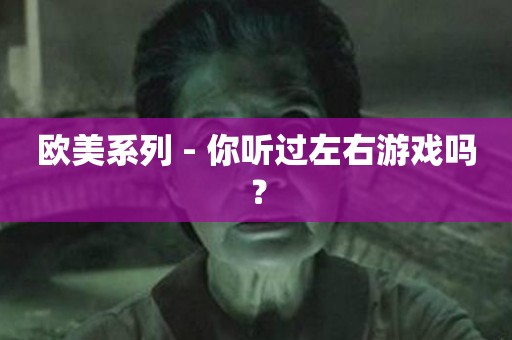
声明
部分内容涉及暴力、血腥、犯罪等,来自网络,请勿模仿
版权:内容只是个人喜好搜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 上一篇: 红色衬衫的女人
- 下一篇: 日本怪谈两篇-《ブサメンの言霊》与《イケメンが好きな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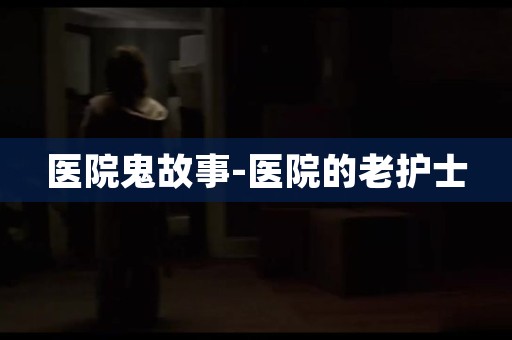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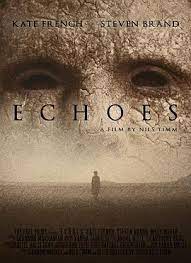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