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付』
这是我小学三年级时经验的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可能有不甚体面的部分先说声抱歉。
文中男人说话的口气谦恭有礼,但因为混杂着独特的粗野与方言,我没办法很好的重现出来,所以统一转写为标準语。不好意思了。
当时我家的人口组成,有母亲那方的爷爷奶奶、父母、姊姊及我。
爷爷出生的老家要重建,于是我们全家人便在拆毁之前过去打个招呼。
那是个满是山林的县市,爷爷的老家也是在山里面。
我平时住的地方虽然也可以说是乡下,但是在县政府所在地附近的平地,所以对到处是斜坡的怀旧气氛感到很希奇,就到週边去探险。
离亲戚家不远的上方有间古老的小神社,里面有小的荡鞦韆和单槓,还有像是玩沙场的地方。
我在周围大致走了一圈,姊姊和爸妈都在正对面小学校的操场上玩耍晒太阳。
我因为很喜欢神社的气氛,就知会爸妈一声「我要再去看看那里」,然后去了神社。
神社里有很大的树,枝条也很壮,树叶相互摩娑的声音令人很舒适。
我坐在荡鞦韆上仰看着树,突然感觉到了他人的气息,于是将视线下移。
视线前方站着一个穿和服的男人。
不是那种漂亮贴实的正式和服,应该是所谓的着流*吧。像是家居服感觉的和服。脚上则穿着木屐。(*着流し:男性不穿袴,单纯只穿和服的轻鬆模样。)
年纪给人的印象大概在二十多到三十前后。
左手肘稍微下面的位置,有条像是割伤的大伤痕。
是住附近的人吗?现在这种时候穿和服,真奇怪的人啊。我一边想,轻轻低头向他打了声招呼「你好。」
然后,原本没什幺表情的男人便很高兴似的弯起了微笑的眼角,回应我的招呼说「你好,小姐*」。
(*お嬢:大小姐(お嬢様)的略称,跟中文称呼女士为小姐不同)
小姐?这一带都是这幺称呼女孩子的吗?愈来愈怪了这个人。我心里一面想着,总觉得有些尴尬,于是把视线挪回了树枝去。
可是呢,那个男人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所以我又战战兢兢的转回去看他。
男人带着有点寂寞的表情注视着我。
我感觉坐立难安,心中判断自己走开好像比较好,就站了起来。
然后,「小姐过得快乐吗?现在幸福吗?」
男人这幺问我,依然是寂寞的神情。
哇!难不成是要传教的人吗。糟糕了。我虽然这幺想,但又顾忌他的表情,没办法装作没看见。
「在学校和在家都过得很快乐,很幸福。」我带着『所以不需要宗教喔!』的意图回答了他。
再说我是真的不觉得自己不幸。
听我一说,男人又用高兴的表情说了。
「这样啊,那太好了。大叔果然没做错啊。」
!????
「真的是太好了。」
完全不懂意思的我,连最初打算回答后就立刻离开的事也忘了,一动也不动的呆立在原位,盯着笑容愈发灿烂的男人看。
虽然无从判断男人是有点怪怪的附近居民,还是危险宗教的传教士,可他并没有恶意,这点很奇妙的传达给我,我坦率的觉得,如果不是这幺悲伤的笑容就好了哪。
正当我打算离开,向他说「那个,我先离开了」的时候,树枝枝叶突然大力的摇动出声,气温也突然骤降。
明明直到刚才都很温暖的,这时却可以说冷得牙齿打颤,阵阵发寒,全身都发抖了。
我往变冷的方向看过去,只见神社的入口有什幺黑黑的东西。
看起来是朦胧的黑色物体,但形状近似人型的黑色不明物。
看到的剎那,强烈的眩晕及呕吐感便往我袭来,「呜……啊……!」我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忍不住呻吟。
滋嚓……滋噜滋啾……滋嚓……
它发出带着湿润感,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声音靠过来了。
距离渐渐拉近后,在黑色之中,能看到好像皮肤溶解后又烧焦,焦黑肌肤般的轮廓,还慢慢能知道它恐怕有头长髮。
一连串让我搞不清楚的状况,以及人生第一次出乎意料的惊骇使我陷入恐慌之中的时候,有谁迅捷地将我的视线从黑色的东西身上挡开。
男人像是要把我保护在身后似的插进我与那东西之间。
「没事的喔,我绝对会保护小姐的。」男人头也不回的这幺说。
我发不出声音,只能对着他那可靠的背影与话语泫然欲泣,不停的点头作为回应。
可是不知道是否因为呼吸困难引起了过呼吸,在那之后的记忆只停留在觉得呼吸好痛苦!!的地方。
头被人抚摸的触感让我张开了眼。
眼前是那个神社。有温暖的阳光及大树。
我坐在鞦韆上,那个男人就站在我的身旁摸着我的头。
我想起黑色不明物的事,猛地看相神社入口,那里已经没有黑色不明物的气息。
放心的吁了口气,但同时又想起男人刚才保护我的事情。
「您有没有受伤!?没事吗!?那个奇怪的东西是……!?」我慌慌张张的问男人。
「已经不在了喔。这点小事没什幺,但可不能让小姐受伤了啊。」他温柔的微笑着。
可是仔细一看,左手腕原本就有的伤痕附近流出了一点血,衣服也到处都是髒汙。
我半哭泣的对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受伤了对不起!……」
想起先前的恐惧,我不停的向他道歉。
因为他一边保护我,一边和那噁心又来路不明的东西对峙。
不可能不辛苦的,我对吓得惊慌失措的自己感到既羞愧又抱歉,忍不住哭了。
从黑色不明物手中逃开的安心感也帮着不让眼泪停下。
「那个……我亲戚家就在附近。伤口要消毒,请您和我一起回去吧。」好不容易按照心意这幺说道。
他便笑咪咪的,用比之前都还要开心的表情说:「果然没做错啊!」
他一边说,比刚才更大力地,夹杂抓搅的动作揉搓我的头。
「小姐长成温柔的人了呢。」
他这幺说后,将手放开我的头。
那手又带到我的眼前,对我递出了什幺东西。
「请收下这个。把它带走吧小姐。」
紫绿黑三色编成的粗组纽*前端,附着直径四公分左右,木製圆黑的东西。
上面雕刻有外公家的家纹。
后来我才听人说,这叫做根付*,是以前佩在钱包之类的物品上的。
(*组纽:日本传统工艺,用有色的细绢丝或棉线编成的细绳。)
(*根付:江户时代流行的小饰物,挂在钱包或烟盒的绳子上,使之夹在和服的腰带里不掉下去,使用例图可参考维基)
正为要不要收下感到迷惑时,他拉过我的手,把它放在我的掌心上。
「谢谢妳。」
我听见男人的声音,该说谢谢的明明是我,我这幺想然后抬头,眼前却已经没了男人的身影。
不只这样,到刚刚抬头的瞬间,周围都还出着暖和的太阳,这时竟变成了晚霞。
应该拿在手上的根付也不见了。
再一次的奇怪状况,让我紧张那个黑色的东西是不是又要来了,便匆忙跑出了神社回去亲戚家。
回到亲戚家,我被外公还有爸爸狠狠的厉声大骂了一番。
因为担心没回来的我,家人和亲戚甚至出动了汽车去找的样子。
我有和家人说要去神社,之后也一直都待在神社里,没想到会弄得这般骚动,实在吓了一跳。
我说我一直都在神社里,但他们说神社一开始就去找了,之后也找了很多次。
可是,并没有在那个狭小的神社用地找到我。
儘管还逼问我到底是去哪里了,可我真的一直在鞦韆那边,并没有说谎所以也没得回答,就算说了那个奇怪的黑色东西的事,也不知道会不会相信,于是我只说出碰到男人的事情。
结果在大家的心中变成『被陌生人搭话还跟着人家走了』这般解释的样子,反而加强了怒火,让我连拳头也挨了。
讲什幺都不被相信,只是一味的挨骂。
难道刚才发生的事只是我栩栩如生的妄想或白日梦吗,就在我开始认真的担心起自己的脑子时,其他亲戚帮我圆场,我总算能回家了。
亲戚把糖果送给被大大怒斥一顿而感到沮丧的我,我于是把糖果放进背包里,这时我注意到了。
那个根付就放在背包里。
慌忙拿出那个根付,问家人和亲戚是不是他们放进来的,但却没有一个人说是他们放的。
不过亲戚中的一个伯父看见根付时说了声「等我一下」便消失在另一个房间了。
这段期间伯母和我说明。
「那个根付平常都是放在神龛*上的喔。真奇怪呢,什幺时候跑进(我)的包里去的?」
(*这里的神龛指日文汉字的神棚,辜狗有图)
「那个,我没有乱动神龛的东西。」
刚刚才被怒斥一顿而已,我在被骂前抢先自主申告。
「(我)的话不可能啦。那地方很高,不用椅子垫脚是碰不到的。」她很爽快的肯定让我安心下来。
这时伯父也回来了。
「那个不是我们家里的哪。家里的还在神龛上喔。」说着他便把根付拿来给我看。
的确是相同的设计。虽然有一个相异点是看起来比我背包里的还古老。
或许是从那个男人手里得到的,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所以没说出来,「这和吉祥物很类似,机会难得妳就拿去吧。可以吧,伯父(指着爷爷)」
于是,放在包里的根付就让我收下了。
等过了一阵子,事件热度退烧后,我去问了爷爷有关根付的事情。
下面就是听爷爷说的内容。
直到爷爷的爷爷那一代为止,爷爷的家系还是人称仁义一家的大家长*。
(*这一般指的是日本黑道的组头。据说过去日本黑道社会曾有自给自足,锄强扶弱的义行,过着与普通市民无缘的生活,因而有”仁义一家”的称呼。)
可是,爷爷的爷爷把两座山份量的财产挥霍光了,从小看着自家衰败的爷爷的父亲于是退出”一家”改去经营商店。
这根付就是那时,带着「即使家业改变,羁绊也不会变」的意涵做出来,分送给”一家”之人的东西。
由于是从爷爷的父亲的遗言听来,爷爷的十四个兄弟姊妹中又没有人跟那条道上有关係,因此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爸爸也是到这天才第一次知道的样子。
接下来只是我的猜测,我在想那个男人,会不会是活在爷爷的父亲那一代的人呢。
而且还是很重视爷爷的父亲的、”一家”的其中一人。
究竟不惜捨弃家业也要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呢,他是不是仍然怀抱着这个疑问就过世了。
我没有灵能力,看见那种可怕的东西,还有不可思议的经验都只有这一次而已,
但我想那并不是一场白日梦。
我现在也每天随身携带着那个根付。
当我觉得要被挫折打倒时,有它在身边,就能很奇妙的涌现继续加油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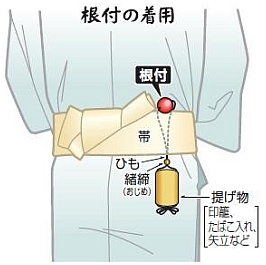
翻译者:哈哈姆特cool6423桑
声明
部分内容涉及暴力、血腥、犯罪等,来自网络,请勿模仿
版权:内容只是个人喜好搜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 上一篇: 没有嘴巴的凯蒂猫Hello Kitty
- 下一篇: 沃尔科特酒店的灵异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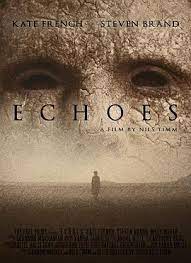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