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周渺然,对,就是那个超异能研究所的成员。所谓超异能研究所,是国际上一个相当神秘的研究组织,专门研究具备超自然能力的人和事。这个研究组织财力物力相当庞大,成员众多遍及各个领域,而且在相应国家具有相当高的行政级别,一旦展开调查,各部门机关都必须无条件配合。多年前,那还是在我刚开始做自由撰稿人时,我有幸帮这个研究所解决了几件案子,从此便和异能研究扯上了无法割断的联系。
如果你读过我的《诡尸》、《暗战》和《酷刑》,那上面这段介绍其实可以自动忽略。
六月份,我在外面旅游了一圈儿回来,刚回到N市不久,魏泊就打了电话过来。
“你过来一趟。”魏泊的声音相当有力,警察是他的第一身份,就跟我的第一身份是自由撰稿人一样,而我们都为研究所帮忙。
一家气氛温馨弥漫着爵士乐的咖啡厅中,魏泊坐在临窗的位置上对我招了招手。
魏泊问我:“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换了号,断了网,出去散心去了,为的就是不让你们找到我。”
“你现在回来也不晚。”说着,魏泊从袋子里取出一本手稿。
确切地说,那算不上什么手稿。说是手稿,你好歹要有字吧。厚厚的稿纸上倒是满图满画的一页又一页,但是一个字也没有,全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相当扭曲的字符。
“说吧,出什么事情了?”
“事情是这样,一个星期前我接手了一件案子,死的是N市一中的一个女学生,那个女学生的尸体检验结果很清楚地表明,她的心脏完全是自行停止跳动的,不是那种临死者心脏衰竭或遭遇不可测力而导致的停止跳动,就像一个开关,说停就停了。按照我们正常人来说你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脏的吧,那属于植物性神经,而那个女生的死法,就像是她告诉了自己的心脏,说,嘿,停吧,别跳了,然后心脏就不跳了,就这么死了。另外,女生死去时就在自己的寝室里,死前无任何痛苦迹象。但听女生的同学说,死前她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这本手稿就是女生死之前留下的。”
“难不成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信息?”
尽管这个说法多少夸张了点,但在研究所里遇到的事情千奇百怪,要说一个女孩子拿一种看不懂的文字预言出2012都没什么不可信的。
【02】
第二天一早,我和魏泊就来到了N市一中。现在正是课间,我和魏泊来到楼下,他拨通了一个号码,那是死者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叫萧薇,魏泊想再约她出来聊聊死者生前的一些情况。就在魏泊打电话时,一个人从身后拍了拍我肩膀,“嘿!”
“王诗雨?”我一脸惊讶,“你怎么在这儿?”
“没想到吧。”王诗雨也用同样惊讶的表情看我,“我在这里当老师啊。”
王诗雨是跟我同届的同学,相当可爱的女孩子,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倒是没怎么注意她,因为她那时太萝莉范儿了。现在这么一看,完全成了一个知性美女。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我陪朋友办点事儿。”
王诗雨朝魏泊看去,她自然知道魏泊的来头,笑眯眯地问我要了电话,然后夹着教材转身离开,嘱咐我别忘了跟她联系。
十分钟后,那个叫萧薇的女孩从楼上下来了。
我们在花园外的长形石凳上坐下来。
“她死前的那段时间的确有些不正常。”萧薇说,“一是整个人显得失魂落魄,经常走神;二是脾气相当暴躁。我跟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一向是一个温和的女孩,这我非常清楚的,但死前那几天,她既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别人找她聊什么问题。然后就是那本手稿,我时不时注意到她在写那本手稿。”
“她死的时候你在场吗?”
“在,”萧薇看了我一眼,“当时是在寝室里,她趴在桌子上写什么,其他人都去打热水了,剩下半个小时就要熄灯了,我开始还没有察觉,直到洗完脚准备上床,才看到她整个人无声无息地趴在了桌上,我以为她是困了,走去拍拍她,结果……”
“其他一点异常都没有?”
“要说异常那就是写那本手稿了,死时那手稿就压在她手臂下。”
“你说她那段时间心情似乎不大好,有没有什么缘由?为什么心情不好?”我问。
“她是相当乐观的一个女孩,那些天她什么也不说,或许她男朋友知道。”
我和魏泊互相看一眼,离开后,魏泊告诉了我一些死者男友的情况。魏泊说,那男孩据说出去旅行去了,我们找到了他在校外租住的房子,人一直没回来。
【03】
“晚上有空吗?一起出来吃个饭吧。”我打电话给王诗雨。
我和王诗雨在门口碰头,然后来到一家火锅店。两人相视而坐,我们边吃边聊。
我问:“你们学校女生的那件事你听说了吧?”
“当然,魏泊不是都来了。”王诗雨歪过头看我,“我觉得你变化有点大。”
“你的变化才大。”
“大吗?我都老了……”王诗雨有点自恋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我是想说你变漂亮了。”
那几天,魏泊那边似乎没什么进展,我便和王诗雨发生了某种情愫上的来往。每天我们发短信互相问候,有空就一起出来喝杯咖啡或者吃顿饭。那时候,我和王诗雨完全没有察觉到,一种潜在的危机正在向我们逼近。
三天后,我接到魏泊的电话。他给了我一个地址,是死者男友的,让我赶紧过去。
这是一片位于学校后的居民区,年代已久。我和魏泊穿过杂乱无章的建筑群来到小道尽头,上至三楼敲门。门开了,是一个相貌俊朗的年轻人。
“请问,你是……”魏泊刚要问,年轻人说,“我知道你是谁,进来吧。”
“我叫顾漳,你们应该知道了,比蔷雨大三岁,高中就辍学了,一直写稿子,勉强维持生计吧,为了陪她,我就搬到了这所学校后面。”顾漳刚刚旅行回来,为的是从失去女友的痛苦中暂时得以解脱,“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部告诉你们,只要能找出她的死因。”
魏泊问:“听说她死前心情一直不好?”
“嗯,我也是听萧薇说的,关于她心情不好这一点,我也是有所察觉的。”
魏泊将那份手稿拿出来,递给顾漳,“你看看这个,能明白上面这些画符的意思吗?”
顾漳摇摇头,“不知道,这是她留下的?”
“是,这是我们手上唯一的线索,现在完全可以排除他杀的可能了,所以你情绪不用激动,然而要说是自杀,这又让我们很困惑,她的死法实在是离奇得很。”
顾漳沉默地看着手稿,忽然起身,在抽屉里乱找一通,翻出一个旧手机来,“这个手机是我出去之前用的,蔷雨死前传给我一段录音的。”
顾漳将那段录音打开,咔,里面传来的是一段混乱的声音,像是磁带被卡带后发出的那种诡异的声音。顾漳皱着眉头,“就是这段录音,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传给我了。”
“交给我吧,我们需要它。”
离开顾漳的房间,我和魏泊都思绪不宁。天空灰蒙蒙的,世界像是一个灯光不足的封闭房间。一本手稿,一段录音,而且全都无法辨识。我又一次感觉到屡次办案过程中的那种无力。在这个奇异的世界面前,人总是显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值一提。
“我们已经把尸体送到研究所了,希望所里的研究部门能帮我们找到更多的线索。”魏泊说,“你先回去吧,这份录音,我拷贝一份传给你。”
回家之后,我收到录音拷贝,便将其载入播放列表,单曲循环。
声音依然是混乱的,那种时而浑厚时而沙哑的声音。我耐心地盯着屏幕上流动的光纹不厌其烦地听下去,中途差点睡着,点几滴眼药水时,我突然从那些声音里听出了一些细微的人声。我找来耳机,戴上之后继续听,果不其然,这录音并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天,我和魏泊来到市区科研所的一台高分辨播音系统前,载入录音反复调试。
录音并非是混乱的,混乱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非常有节奏的声音。
那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他像在讲故事一样朗读着什么,依稀可辨其中的一段:
他把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擦擦,想使手指松动松动。可是手指张不开。也许随着太陽出来它能张开,他想,也许等那些养人的生金槍鱼肉消化后,它能张开……
再下来还有:
多年以后,奥莲雷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孔多是个二十多户的村庄……
我说:“这不是《老人与海》和《百年孤独》里的片段吗。”
“这是什么意思?”魏泊问我,我说不知道。
“莫非是想通过这些提示我们什么?”
“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想,蔷雨是从哪儿得来这段录音的?”我说,“如果她想用这段录音传达什么给活着的人,为什么不自己录下来?”
“你的意思是,蔷雨无意间录下来的?那她又为何要传给顾漳?”
“不知道,如今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04】
星期天早上,我被一阵电话铃吵醒。是王诗雨,她问:“怎么,还在睡觉吗?”
“呃,是,这两天有点累啊。”
“要不要出来逛逛,正好一起吃早点。”
我洗漱完毕到约定的地点与王诗雨见面,两人在一家粥馆里吃了早点。天光变得更加明朗,看样子是个晴天。来到公园外,我们坐在园外的花坛上聊天。没多久公园里便热闹起来,练剑的老人,闲逛的情侣和约会的学生。
我们聊了没多久,我便牵住她的手,而她没有拒绝。
魏泊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和王诗雨聊最近学校里的事。魏泊告诉我说,死者的尸体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黄文斌也回N城了,并来协助调查。
赶到市医院,黄文斌坐在桌子后面笑眯眯地看我。他是N市里非常著名的医生,另外也是研究所分派到N市的总调查。
黄文斌将我们带往另一房间,开灯之后,我看到了光墙前贴着的一张张大脑光片,桌子上则是一个黑色的袋子,上面有研究所的标志。
黄文斌就光片讲解了一通,我让他说通俗点,他说:“我们最终选择了开颅,研究结果表明,死者蔷雨的大脑中产生了一种物质,一种我们目前无法解释的物质,我们暂时称之为X,我想这次超自然的对象,就是这个X。”
“这X有什么特点?”
“这个很难解释,因为它是无形的。”黄文斌皱着眉头说,“完全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认识范畴,当我们将蔷雨的脑切片拿出来反复做各种检验时,我们发现脑切片当中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而发出这种力量的源头,就是被我们称为X的物质,我们试图用脑部各部位不同的地方进行分析,惊讶地发现,这种X物质竟然具有多重奇怪的能力,第一,它可以产生水质,我们曾将脑切片放在干燥的纸巾上,纸巾会被打湿;第二,它偶尔又可能具备吸水的效果,甚至可以将整个湿巾上的水吸收,而这仅仅是它作用于与水有关的物体所产生的效果,我们怀疑它作用于不同物质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至于它对神经的干扰,我们则很难得出确凿的实验结果,因为想得出结果,就必须捕捉X,并将其注入人体。”
“至少就目前而言,X很可能对蔷雨的身体起过某种无法解释的作用?”
“可以这么说,虽然并不准确。”黄文斌皱了一下眉头,“你们这边有什么进展吗?”
魏泊看我一眼,“哦,对了,昨天下午我见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
“谁?”
“蔷雨的父母。”魏泊定定地看着我,“她父母说,蔷雨曾经也出现过情绪失常的情况。她的家庭并不是很富有,父母是一般的工薪阶层,父亲是个相当严格的人,家里对她的期望值也比较高,一直以来,蔷雨的学习都很好,但是蔷雨在学习上是有受迫倾向的,这一点在她老师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她父母说,其实早在蔷雨中考那一年,蔷雨就出现过一些情绪上失控的反应,她不想让父母失望,就逼迫自己要天天学天天学,表面上又是个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的女孩,一旦进入受逼的学习状态,很容易导致抑郁。临走时,她母亲透露说,在中考那年,蔷雨甚至一度有自杀倾向。”
黄文斌敏锐地问:“可是蔷雨死前并没有什么压力吧?”
“没有。”魏泊说,“萧薇说,她当时情绪上的突变是非常不正常的,仅仅是因为学习压力,也不可能将一个人变成那种状态。”
“会不会是那手稿里附着有X?”我问。
黄文斌眼前一亮,“倒是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目前无法捕捉X,只是从侧面推导出它的存在,既然无法捕捉,那我们更无法确定其存在的方式与传播途径。”
【05】
第一次去王诗雨的房间,我便注意到了她客厅角落里的那架吊钟。
那是一架看上去有些年代的吊钟了,相当陈旧,漆色斑驳,我问王诗雨是从哪儿弄来的,她说是旧货市场淘的,勉强能用,但时不时会出问题。
王诗雨系上围裙后去厨房做菜。我便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不知为何,我的注意力始终被那架吊钟吸引着。沉静的钟体里,那个吊摆来回摇晃,像是有什么秘密在里面随着时间荡漾。当我看得入迷时,王诗雨用五指在我眼前晃动,“喂喂,看傻啦!”
“啊,怎么?”
“让你来尝一下菜。”她笑着拉我起身,这时,忽然有人敲门。
她走去开门,跟门外的人说了一会儿,收进来一个包裹。
她将包裹拆开,上面塞着一层裹成团的报纸,看到报纸下面的东西,她微微怔了一下。
我没有问她那里面放的是什么。
这天,我和她一同吃了饭,下午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场很感人的电影,把我都感动得够戗。但是王诗雨一脸冷静,无动于衷,她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也同样心不在焉。
离开时我问她:“你今天心情不好?”
“没有啊。”
我捏握了一下她的手,她嘴角扬起一丝微凉的笑意。
从王诗雨家中出来后,我在街边买了一杯奶茶,漫无目的地前行,就在经过中央公园外的一条荒僻街道时,一个乞丐瞬间拉走了我的注意力。
乞丐正用一截粉笔在地上随意乱画,我起先并未太在意,回头一看,地上的字符居然和蔷雨那本手稿上的字符颇为相似!
我走过去,看着地上的字符,盯住那个乞丐,直到他的目光抬起来。乞丐冲我嘿嘿一笑,我相当严肃地问他:“你认得这些字符?”
他举起身边那个锈迹斑斑的小钵,我不耐烦地掏出了十块钱给他。
他把粉笔丢开,我再一次问他,他摇摇头,“我也是跟别人学的。”
跟别人学的?我一脸疑虑,看着那些字符,发现乞丐所画出来的并不像蔷雨手稿上的那么潦草无章,很多字符是紧密连接的,似乎在表达特定的意思。
“那你知道这些字符的意思吗?”
乞丐懒散地摇了摇头,我又问是谁教他画这些字符的。他说那个人不在这边,只是偶尔在另一条街上遇见,那人性格也甚是古怪,经常揣着粉笔。那条街比较荒败,我问乞丐能不能领我去,他再一次将手中的小钵举了起来。
我谨慎地跟着乞丐转入一条偏僻的街道,乞丐将我领到一面坍塌半面的墙壁前,我不由地吃了一惊,墙面全部是类似的字符。
魏泊和黄文斌赶到这里,看到墙上的字符后,两人也同时露出诧异的神情。黄文斌用带来的相机拍下了墙上的信息,魏泊打电话给局里安排,让他们过来将乞丐带走,进一步调查以保证能找到那个人。
经过一番寻找和核实后,三天后的夜里,我们在魏泊的办公室见到了那个名叫许峰悲的中年男子。他看上去跟我想象中一样苍老、不修边幅。
明亮的灯光下,许峰悲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我们三人,嘴角挂着一丝神经质笑容。
“我们找你来是想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希望……”
魏泊还没说完,许峰悲就邪气沉沉地笑了起来,口吻有点变态地问:“死人了吧?”
我们三个人互相看看。
“你怎么知道是死人了?”魏泊问。
许峰悲咯咯地发出一丝尖利的笑声,“肯定是,肯定是。”
魏泊用警示的眼神看他,他立马又收起笑容,变成一副极为严肃的模样。
黄文斌将照片放到桌上,“这墙上的字符是你写下的,对吗?”
许峰悲沉静地点点头,这时他的反应才和他的外貌年龄相匹配,“是的。”
“你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一种密码。”
“密码?什么密码?”
“人类内心的密码,灵魂的密码。”许峰悲一脸平静地看着我们,“一直以来,我都在以这个为对象作各种研究,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具备这种深层次的沟通力量。”
“我不大了解你的意思。”我说,“你能描述得通俗易懂些吗?”
许峰悲扬起脸来看我,定定地看了几秒,问:“你恋爱了?”
我蓦然一怔。
许峰悲忽然起身,龇牙咧嘴地从桌后咆哮般冲我逼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你恋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还没说完,他又一脸委屈,开始变得哭哭啼啼,甚至略带抽搐,温柔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一定要珍惜她啊,一定要珍惜……”
许峰悲的状态最终使得我们打消了继续询问的念头。我们三人来到陽台上抽烟,魏泊说这人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
“可说不定这个神经病比一般人看到的更多。”
“先让他情绪稳定一下吧,另外,魏泊你派人调查一下他的具体身份社会履历,我倒觉得他说的话一点也不神经,而且他的确知道什么。”
【06】
许峰悲的个人信息令我和黄文斌大吃了一惊。父亲是一个哲学家、心理学家,母亲是社会活动家、宗教与科学联系发展研究者,他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个人天赋,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尤为显著。曾受到过全世界几所著名高等学府的游学邀请,但是在二十一岁那年辍学,不再向心理学方向深入研究,慢慢销声匿迹,这么多年来,他的社会履历一片空白。对于他究竟干什么,有人认为他属于神童早夭,彻底沦落为了一个俗人,有人则认为他是在研究某种更为神秘的领域。最让我们吃惊的是,他还曾担任过超异能研究所的心理顾问。
我和魏泊希望黄文斌向研究所上报,批准我们阅览一些和许峰悲有关的资料,但没有获准,据称那些资料涉及到相当复杂的超自然问题。
接着,黄文斌回研究所,继续去捕捉那种X物质。我和魏泊将手稿、录音和许峰悲的信息反复推敲,试图从中找到一条线索,忙得天昏地暗。
就是在这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关键。
王诗雨割腕自杀了。
我赶到医院时她已经脱离了危险期,是她的邻居将她送来的。
我失魂落魄地出现在王诗雨的病榻前时,她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只是冷冷地闭着眼睛,脸色冰凉。我守了她整整一天,可是她一句话也没说。
夜里我在她的床前睡着了,第二天陽光照射进来时,王诗雨的手轻放在我的头发上,轻柔得像是根本不存在。我抬起脸,用无比深情的目光看着她,那一刻,我感觉到她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以前我曾看过无数人的哭泣、哀号,痛失亲人后的绝望,但我从没见过她那样的眼神,那种贯穿别人灵魂的眼神,像是山上流下的泉水被灌入了湖泊,那是一种潺潺的哀伤,却比任何放肆的痛苦要来得凛冽千倍。
我拿走了王诗雨的房门钥匙,既然她不肯说,我只好独自寻找。
开门后,我走进房间,客厅里一片死寂。我的心情相当沉重,就算看到明亮的沙发、精致的壁纸和一尘不染的桌椅,仍有一种难以挥去的悲哀坠挂在我的心头。当我想起我和王诗雨在这里度过的一些美好瞬间,我的眼睛甚至都湿润起来。
我吐出一口气,脚步徐缓地走到盥洗室。和我想象的一样,地上有一片血迹,而盥洗台上那刺眼的刀片如同锋利的冰凌使人心头涌起一股寒意,它看上去那么安静,很难使人将其和死亡联系起来。
我推开了卧房的门,房间里一尘不染,光线有致地落在临窗桌前。我想起自己来此的目的,思索一阵,记起上次王诗雨收到的那个包裹,我猜测里面的东西一定非比寻常。
我找到那个箱子,取出铺在上面的报纸,下面放着的是两件毛衣。两件小孩子穿的毛衣,上面是简单的图案,看得出来,织得很用心。
就在这时,房间里传出“咚”的一声,我惊惶四顾,才想起是那架吊钟的声响。来到客厅,我考虑要不要将盥洗室的血迹清理掉,就是在这一瞬间,我听到那声音。
那男子的朗读声。
没错,那细微的朗读声就是从屋中传来的。我闭上眼睛,跟随声音的来处往前走,最后撞在了吊钟前。
当我将手放在吊钟上,那声音就变得更加清晰了,他朗读的是《简·爱》里的片段:
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但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悲伤,只是感觉人生中最空旷的地方被人触碰了。
我闭上眼睛,手抚着那口吊钟,摁下了手机的录音键。
【07】
带着录音的内容,我朝顾漳租住的房间跑去。我恍惚之间明白了什么,虽然并不能确定,但是种种线索纠缠在我的脑袋里,只能给出这个合理的解释。要知道,作为研究所的成员,黄文斌是医生,魏泊是搜集信息的高手,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自由撰稿人之所以能成为其中一员,就是因为我具备比较罕见的超自然联系思维,以往的种种事件也表明,我的确可以将那些碎片式的事物联系起来,找到超能力所在。
我带着录音敲开了顾漳的房门,开门后,我表明来意,让他关上房门,拉上窗帘,在昏暗的屋内播放了那段录音。
果然,和蔷雨给的那段录音一样,播放出来的是较为混乱的声音。顾漳一脸不解地看着我,正想问为什么,我示意他不要说话。慢慢地,录音之中一些声音被分解出来了,接着,房屋里响起了一个低沉的男子说话声。
他在朗读!又是朗读!
顾漳睁大眼睛,一脸惊诧,我则细细分辨着那朗读声。它像一段旋律,高低起伏,由此到彼,环绕在我们身边。我跟随它的强弱变幻位置,感觉到它是从墙壁中发出来的。
我抬起脸,环顾这间房子,“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让人难以承受的事。”
顾漳正要发问,我没有时间,告诉他最好搬出这间屋子,然后给魏泊打了电话,要他帮我查找一下这片居民楼的历史信息。接着,我再次去了王诗雨家,将吊钟照入手机,又去王诗雨曾提起过的旧货市场询问。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没有任何票据的情况下寻找那架吊钟的主人,寻找它曾经待过的地方,最终在一家非常有名的旧货店里得到了店主的帮助。一切跟我预料的一样,这架吊钟,是从顾漳那片居民区里收购来的。
那架吊钟曾经的主人,是一个名叫王季贤的男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出手了那架吊钟。
我马上打电话给魏泊,要求他核实住户信息,包括一些户籍资料。事实表明,当时王季贤就住在顾漳所在的这片居民区中。魏泊在电话里问:“你发现什么了?”
“还记得录音吗?”我说,“那个朗读者,应该就是王季贤。”
“什么朗读者?”
“录音里那些朗读声,是王季贤留下的。”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魏泊问,“王季贤给了蔷雨那段录音?”
“不,王季贤已经不知去向了,那段录音是蔷雨自己录的。”
魏泊还是没听明白,我说:“我的猜测是,王季贤将声音储存在了自己生活过的地方,也储存在了自己使用过的物体中,然后,某种现象使得王季贤的声音复苏了,蔷雨就将这种声音录制了下来,而且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也录到了同样的声音。”
“那么说,蔷雨的死,跟王季贤有关?”
“他应该是无心的,你现在马上去找王季贤的资料,把这个人带回来!”
下午,我简简单单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去医院看望王诗雨。她仍旧一言不发,不愿意说话,只是偶尔像个孩子一样看我。盯着她那湖泊一般的深眸,我又一次体会到上一次体会到的那种悲伤。不错,我就是在这种体会中大胆假设的。当我情绪低沉的那一刻,我忽然在想,我们为什么快乐,为什么悲伤,为什么看到别人的痛苦会落泪,为什么看到心爱之人的笑容会感觉温暖,这是一种情绪的力量,一种强烈的感染。我在想,当初让蔷雨发生异常的,会不会是同样的力量呢?
我喂王诗雨吃了饭,看着她像小姑娘一样嚼食时的可爱样子。我想,我一定能将她带出这家医院,无论她是被什么困厄在悲伤之中。
天黑之后,魏泊打了电话。接通后,那头先是一阵沉默,更像一句叹息。
“他死了,对吗?”我不假思索地问。
“是。”
“死了多久了?”
“搬出那片居民区不久后,回到家乡,自缢身亡。”
“那么说,我的猜测很有可能是对的。”
魏泊问:“你已经搞明白了?”
“也许吧,我想许峰悲一定能给我们更系统的解释。”
“要将他找来吗?”
我说是,挂上电话,俯身抚摸了一下王诗雨的脸颊,“诗雨,我不会让你陷进去的,你等着我,我会带你离开。”
她仰起脸,用纯净得近乎令人窒息的目光与我对视。
【09】
那的的确确是一段相当悲伤的故事。
那些天,我在医院里陪伴着王诗雨,以防她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
一个星期后,我从许峰悲手中得到了王季贤的故事,那个从手稿情绪中解答出来的陈年往事,当然,事情的前前后后,许峰悲作了一定调查,以让整个故事完整了:
20世纪九十年代,王季贤喜欢上了一个女子,两人感情甚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女子很不幸发生了意外,变成了植物人,然而王季贤丝毫没有放弃,因为他相信自己很有可能唤醒爱人,于是每天守护着爱人,为她朗读各种书籍,朗读形形色色令人落泪的故事,因为爱人出事前,最爱的就是听他朗读。三年的时间里,王季贤就这样不离不弃地守护着沉睡的爱人。然而王季贤的家人却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不想儿子将自己的幸福赌在一个没可能醒来的植物人身上,于是强迫其离开。家人知道对王季贤施压无济于事,于是转向对女子的家人施压,最后迫使王季贤离开了医院。但王季贤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租了一间房子,开始跟其他女孩交往,却每天夜里在屋中朗读,声音录下来,寄到医院,让医院护士播放给沉睡的爱人,他仍旧相信,自己所爱之人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这件事被发现之后,王季贤家人不得不彻底将其隔离开,并且反复施压,最后导致了王季贤的崩溃。就像所有悲情故事所注定的那样,最后,王季贤自杀了。
我在电话里问许峰悲:“那么女孩呢?”
“醒了。”许峰悲的声音充满了哀悯的平静。
“到底还是在王季贤的朗读声中醒了过来吗?”
“嗯,但是记忆上有些损伤,而且生活自理能力也不高。”
我沉默下去,电话那端也是一种无声无息的回应,我想,人们的内心都是共通的。
我转过脸,看着落进窗户的陽光,对王诗雨笑了笑。
不久后,许峰悲接到了黄文斌的邀请。黄文斌需要许峰悲的理论支撑继续研究那种X物质,也就是说,黄文斌的发现加上许峰悲的理论,表明王季贤的确是异能人,一种操控情绪的异能人。他可以物化情绪,并使之在人体产生那种奇异的物质,而正是X这种物质,可以影响人体的生理机能以至于造成蔷雨那奇异的死亡。许峰悲接受了黄文斌的邀请,从此他也不需要拿自己的身体当成实验对象以至于搞得自己疯疯癫癫了。去研究所报到之前,许峰悲决定将那本手稿交给当年王季贤的爱人,我说我也要去。
或许看到她,我能更加明确如何将诗雨拉出悲伤的旋涡。
然而去之前,一个女人找到了我,她自称是诗雨的母亲。
多年前,她抛弃了一个女婴,而至今还在为自己的心灵赎罪。
最终,我没有去见王季贤当年的爱人,而是选择留下来,我相信我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去感染诗雨,化解她心里的悲伤。
正如王季贤当年可以唤醒那个女子一样。
声明
部分内容涉及暴力、血腥、犯罪等,来自网络,请勿模仿
版权:内容只是个人喜好搜集,如有侵权请联系处理。
- 上一篇: 大驱魔师事件簿:华特哈勒伦(终)
- 下一篇: 生死之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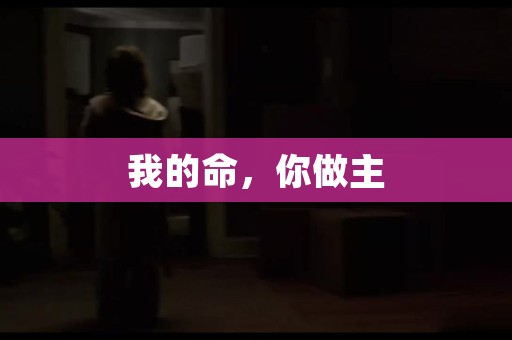




















发表评论